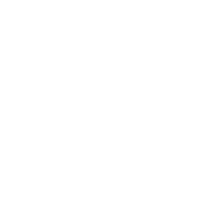“俞龙戚虎”短长论

俞大猷和戚继光是明代杰出的抗倭将领,被时人誉为“俞龙戚虎”,但他们的遭遇却不一样,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有区别。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且来回顾一下他们的经历。
俞大猷(1504-1580年),字志辅,号虚江,出生于泉州洛江区河市(即原晋江河市)一个下级军官家庭,祖籍安徽凤阳。俞大猷少时,家境贫困,依靠母亲杨氏编发网和亲友资助,维持生活和读书。他勤奋学文习武,勇敢机敏,在清源山下读书时,常独自一人在虎乳岩锻炼手脚。后来当秀才,又拜泉州名儒蔡清之门徒王宣及军事家赵本学为师,学习《易经》与兵书;向精通荆楚长剑的李良钦学习剑术。父亲死后,他弃文就武,承袭百户官世职。他的一生历仕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戎马舟楫,转战南北,战功显赫。他曾在山西边境击退蒙古俺答的侵扰,在广西击败安南(今越南)范子仪的进犯,只身平定过海南岛的叛乱,又纵横东南各地,由福建转战江浙,继而两广,屡破倭寇大盗,他历经大小百战,“俞家军”声望不在“戚家军”之下,若论经历的战斗次数,歼敌多少,平服的海盗山贼数量这样的硬指标,俞大猷则超过戚继光,且比戚继光更有传奇性。

然而俞大猷的一生却很不顺利。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俞大猷中武举人。当时海寇频发,俞大猷“上书监司论其事。监司怒曰:‘小校安得上书?’”连一个小小的百户职位都因此丢掉了。后来参加全国武举会试,写了一篇《安国全军之道》的策论,深受兵部尚书毛伯温的赏识,荣获第5名武进士,授任守卫金门、同安一带,也不过一个小小千户。一直到朱执巡视福建时,见俞大猷讨贼有方,“荐为备倭都指挥”,他才有了用武之地,但还是受到多方掣肘,而且战功经常被上司冒领甚至抹煞。嘉靖二十八年,俞大猷大败安南入寇,“追战数日,生擒子仪弟子流,斩首千二百级”,但“事平,严嵩抑其功不叙,但赉银五十两而已”。嘉靖三十一年,倭寇进犯浙东,攻陷数处要地,“大猷邀诸海,斩获多,竟坐失事停俸”。同年,倭寇以两万之众进犯金山,俞大猷初战失利,但随后“大破贼于王江泾”,取得战役胜利,不但功劳被赵文华、胡宗宪抢去,反而“坐金山失律,谪充为事官”。嘉靖三十四年,倭寇进犯苏杭,屡败赵文华所统帅的官军,俞大猷往援,敌退,“巡抚曹邦辅劾大猷纵贼,帝怒,夺其世荫,责取死罪诏,立功自赎”。嘉靖三十六年,海匪王直被诛之后,其部毛海峰盘踞舟山,官军围攻了一年,海盗主力未被歼灭,“余贼遂扬帆而南,流劫闽、广”。尽管俞大猷“先后杀倭四五千,贼几平”,仍然成了胡宗宪推卸责任的借口,“委罪大猷纵贼以自解。帝怒,逮系诏狱,再夺世荫”。这一回,幸亏锦衣卫的长官指挥使陆炳帮忙,慷慨解囊三千两银子,“密以己资投严世蕃解其狱,令立功塞上”,俞大猷才侥幸得免。到了嘉靖四十一年,俞大猷已“威名震南服”,并以数建大功,为将廉洁,受到了朝廷的认可,但“巡按李良臣劾其奸贪”,再被“诏还籍候调”。到了万历初年,已近花甲的俞大猷出任福建总兵,因为“海寇突闯峡澳,坐失利夺职”。最后不得不“三疏乞归”,解甲归田,77岁时病逝于家中。
比之俞大猷,戚继光的经历却顺利得多。戚继光(1528-1587年),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山东蓬莱人。戚继光祖辈均系明代将领,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其父戚景通熟读兵书,精通武艺,治军严明,曾任都指挥使。戚继光自幼生长在将门,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军事生活的熏染,很早就抱有忠心保国之志。袭任登州卫指挥佥事后,他以祖父辈为榜样,“留心韬略,奋迹武闱”,决心为保卫海疆做出贡献。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王朝为抵御蒙古鞑靼部南袭京城,把蓟州(今天津蓟县,当时指山海关至居庸关一线)列为边镇,由山东、河南抽调官兵戍防。戚继光曾一连5年,每年都有一段时间率领本部人马到这一带执行戍务。在此期间,他曾两次上书明廷,献备敌方略。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戚继光升任都指挥佥事,主管山东防倭军务,统辖3营24卫所,防线自江苏、山东交界处,一直延伸到山东半岛的北端。海防线这么长,而卫所的兵力有限,戚继光开动脑筋,摸清倭寇活动规律之后,按照时间和地段重点设防,同时对卫所进行整顿,加强训练,严肃纪律,提高战斗力,使倭寇不敢窜扰。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浙江地区倭患严重,戚继光调浙江任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率军抵抗倭寇。他见旧军素质不良,即向上司提出“招募新兵,亲行训练”的建议,后至义乌招募农民、矿工3000余人,组成新军,称“戚家军”。这支军队经过严格训练,成为熟悉军纪、法度,熟练手中兵器,能够奋勇作战的队伍;他还根据江南水乡的特点,改造队列体制,创造了鸳鸯阵法,使长短兵器配合作战,用火器、弓箭掩护,在抗倭作战中发挥了巨大威胁力。嘉靖四十年(1561年)五月,倭寇集结船只数百艘,人员万余,窜犯宁海、奉化、桃诸等浙江沿海县城,并企图攻占台州府城。戚继光率领戚家军,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运用偷袭、伏击、快速奔袭等战法,打得倭寇晕头转向,莫知所措。次年,倭寇大举窜犯福建,沿海城镇受到倭寇荼毒,戚继光率军驰援,一举捣毁倭寇在横屿(今福建宁德城外海中)的老巢,取得首战胜利。随后连续发动攻势,扫平倭寇据点多处,杀伤倭寇无数,击退了倭寇的进袭。转年,倭寇又纠集残部,掳掠边城,戚继光再援福建,与巡抚谭纶、总兵俞大猷和广东总兵刘显通力合作,平定了闽、粤沿海的倭患。隆庆元年(1567年)戚继光被张居正调到北方,镇守蓟州。在镇16年,对练兵、治械、阵图等多有创建;边备修饬,节制严明,军容为诸边之冠。由于设备稳固,部队精练,鞑靼未敢轻易来犯。万历年间,蒙古部落曾3次骚扰边城,均被击败。他一生中几乎没有受到多少责难排挤,理想也大部分实现了,官位也做到了武官的最高级别。
俞大猷和戚继光的遭遇如此不同,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我以为首先是性格上的差距。明代从洪武朝开始,便出现重文轻武的趋向,大约经过一百年,文官集团进入成熟阶段。文官作为总督巡抚,有权指挥各级武官。在军政方面,人事的任免以及补给、交通各项也统统由文官主持,武将实际上只有亲自带兵上战场厮杀的权利,而战争的结果,也要由文官上报,文官想给武将报多少功,或者想加什么罪,都由文官说了算。在这种情况下,武将只有巴结文官,才能使自己获得公正的待遇。俞大猷为人正直,既不迎合权贵,也不讨好上司,这样的人注定要遭到同僚的嫉恨和排挤,纵有再造本朝军事力量的宏图和能力,也无法实现。
戚继光在这一点上却比较灵活,最明显的是他在文官集团中找到了两个掌握实权的大臣的支持,这就是谭纶和张居正。谭纶在文官集团中是一个特殊的人物,进士出身,长期在东南滨海地区任职,累迁至福建巡抚。他对戚继光的军事才华十分赏识,戚继光之得任福建总兵,也主要出于他的推荐。1567年,谭纶升任蓟辽保定总督,负有防御京畿的重任。不久他就提议把戚继光调到他的辖区中担任最高将领。
张居正在戚继光北调的前几个月才出任内阁大学士,他在入阁之初就有重整军备的雄心,他对戚继光的军事才能也早有耳闻,谭纶将戚继光调蓟州的事他就帮了忙。戚继光建议把北方各镇数万名士兵交给他训练3年,由于计划过大,在政治上和技术上都有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未能实现。但中枢政府批准了他的另一项建议,即把他在浙江所训练的一部分士兵调至蓟州,并陆续增加至2万人,使戚家军成了蓟州军队的中坚。谭纶建议该区的文官不得干预军事训练,并且主张戚继光在3年的练兵期内可以不受监察官的批评,遭到文官们的猛烈反对,张居正便说服皇帝朱笔批示接受兵部和都察院的建议,要求监察官明白练兵的重要,责成他们“和衷共济”,并把他们对蓟州防区的巡视限为每年一次。为避免戚继光遇事掣肘,他又不动声色地将蓟州辖境内凡是故意和戚继光为难的文官和其他高级将领陆续调往别镇。如此等等,让戚继光自己就感觉到只需专心于军备而不必参与政治,因为凡是应当安排的事,都已经由谭纶和张居正安排妥帖了。张居正对戚继光的关照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谭纶去世后第二年,张居正回江陵葬父,他生怕这短期的离职引起戚继光的不安,还特地写信通知戚继光,说明接任蓟辽总督的梁梦龙,在翰林院与他有师生之谊,并多赖其提拔,让戚继光放心。戚继光正是因为有了谭纶和张居正这样的领导和靠山,才使他的军事理想得以比较顺利地实现。
戚继光之所以能引起这两个人的格外关注和支持,固然由于戚继光自身的军事才华,和这两个人对国家武备的关心,同时与戚继光主动争取恐怕也有关系。戚继光与谭纶的关系历史上缺少记载,但与张居正的关系却有一些记录,比如张居正回江陵奔丧时,戚继光派出了一整连的鸟铳手作为护卫,大概是张居正觉得太招人眼了,才只选择了其中6名随行,作为象征式的仪仗;戚继光还曾让他的兄弟给张家“馈送”礼物,张居正也只象征性地收受其中的一小部分,把其余的“璧诸来使”,可以隐约看出礼物的贵重;据戚继光的好友王世贞写的《张公居正传》说,因为张居正好色,后来调任兵部尚书的谭纶曾把房中术传授给张,戚继光则曾用重金购买称为“千金姬”的美女作为礼品奉进。从这里也可以隐约看出谭、戚、张三人之间的密切关系。类似上述这样的事情,你可以说它是“报恩”,也可以说它是行贿,因为这样做的实际结果是,他们从张居正那里得到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支持,以至在张居正死后朝廷清算张居正的运动中,许多人都认定戚继光是张居正的同党。而这样的事情,放在俞大猷身上大概是不会做的,所以《明史》本传把戚继光和俞大猷比较,说戚“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估计也是从这个方面说的。
其次是俞大猷比较理想主义,认定的事不容易转圜,而戚继光则比较实际,能够适应环境。比如战术全面现代化的建议,曾经被俞大猷提出过。他准确地指出,倭寇的特长是娴习陆战,水战的技术反而低劣。所以他主张以有效的战船和火炮歼灭倭寇于海上,根本不让他们有登陆的机会。在战术原则上,在他所著的书里也明白指出:“海上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他给总督的禀帖中,曾经请求把陆军军费的一半用来配备水师。但纵使俞大猷的声望和战绩都十分卓著,这些有益的建议却始终没有被采纳,为什么呢?因为俞大猷的建议所牵涉的问题和将要引起的后果,已经超出军备而及于政治。他要求亲自率领“闽广大船数百艘,兵数万”,如果一旦成为事实,有关各省的财政就要从原来小单位之间的收支而被集中管理。与之相应,这些后勤机构的人员必须增加,而且必须一扫苟且拖沓的办事作风,保证规格和数字的准确,才能取得预期的行政效率以与现代化的军事技术相配合。而且和他们往来的各个机构,也必须同样地注重实际。然而这与重文轻武的观念背道而驰,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相形之下,戚继光的方案就比较现实。他没有去触动整个的国家体制,而只做他职责范围内力所能及的事。他从1559年开始招募3000名士兵。两年之后,兵员增加一倍,1562年更扩大为10000人。可是他的部队从来也没有一个后勤司令,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军需处和兵工署。在整个国家机构之中,也没有委派过向他的部队作后勤供应的专职人员。他部队中的装备和武器,来源于各府县的分散供应。这种情况自然不能保持武器的质量,有的鸟铳铳管常有炸裂的危险,有的火炮铅弹与口径的尺寸不合,有的火炮导火线无法燃点。有鉴于俞大猷的壮志难伸和火器的实际情况,戚继光所拟订的战术,仅仅把火器的应用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火器为接敌之前用,不能倚为主要战具。”在练兵的后期,他规定12个人的步兵队配备鸟铳2枝,一局(相当于一连)的鸟铳手,必定要有一局的步兵“杀手”协同作战,并由此而创造鸳鸯阵法,在实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又比如按照俞大猷使军队现代化的计划,要求兵精械利,把原来两个士兵的军饷供应一个士兵,以部队的质量来代替数量。戚继光的看法则不同。他认为帝国的军队是一支全能性的军队,也是一支长久性的军队。它经常的任务是面对内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具体地说,就是镇压内地农民和边区的少数民族。而我国幅员很大,这种所谓造反作乱的地点极难预测,镇压的任务也不是一支高效率的机动部队所能完成。在多数情况下,官军会被造反者死死吸住。因此,数量的多寡就成为决定胜负的因素。除此以外,俞大猷计划中所创建的精锐部队,他们领取优厚的军饷,又不能和社会上的其他部门对流,这样一个浮游于社会上的军事团体非但不能解决上述的社会问题,相反还会引起新的社会问题。再往下推求,俞大猷要求建立现代化的海军以拒敌于国门之外,作战的目的,则在消灭国际贸易,也和世界历史趋势相反。再比如戚继光的募兵原则是只收农民而不收城市居民。他认为来自市井的人都属于狡猾无赖之徒。这种观点,虽然有它的片面性,但实际上,在城市中有固定职业的人是极少自愿从军的。士兵为社会所普遍轻视,其军饷也相当微薄,城市中的应募者绝大多数只是把兵营当作解决食宿的救济所,一有机会就想另谋高就。这样的士兵如何能指望其奋勇杀敌以至效死疆场?所以戚继光订立了一条甄别应募者的奇特标准,凡属脸色白皙、眼神轻灵、动作轻快的人一概摈诸门外。因为这种人几乎全是来自城市的无业游民,一旦交锋,不仅自己会临阵脱逃,还会唆使周围的人一起逃跑,以便一旦受到审判时可以嫁祸于这些言辞钝拙的伙伴。在这个标准下招收来的兵员,都属于淳朴可靠的青年农民,而“鸳鸯阵”的战术,也是针对这些士兵的特点而设计的。他明确地指出,两个手持狼筅的士兵不需要特别的技术,膂力过人就足以胜任。而这种狼筅除了扫倒敌人以外,还有隐蔽的作用可以使士兵壮胆。
戚继光的求实精神还表现于使革新不与传统距离过远,更不大事声张。他的部队保留了古老而朴素的农村作风,有时也和卫所内来自军户的部队并肩作战。他们日常的军饷,大体和在农村中充当短工的收入相等,但另设重赏以鼓励士气,一个敌军的头颅,赏额高达白银30两。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他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他看清并适应了当时的政治,而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这是在当时环境里唯一可以被允许的方案。我认为是很对的。至于在一个以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之内,谁想要极端强调军事效率,提倡技术的发展,而导致军人和文官的并驾齐驱,哪怕他能举出无数动听的理由,在事实上也是绝对办不到的。
从上述情况来看,我以为俞大猷的根本问题出在书生气太足,过于认真,过于理想化。他不知道在那样一个官僚统治的时代,要想洁身自好,处处“以古贤豪自期”,坚持原则,不肯妥协,不肯迁就现实,结果只能处处碰壁。而戚继光的成功,恰恰也在于没有那么多的书生气,处事比较灵活,能够审时度势,该进时进,该退时退,该拉关系时拉关系,只要能达到目的,哪怕只能部分实现,也在所不惜。戚继光是一介武夫,又是一位饱学儒生,在同时代的高级将领中,除了“少好读书”的俞大猷之外,可以说无与伦比。在平常的谈话中,他可以随口引用儒家的经典和史书上的教训,像他这样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他的某些做法是违背儒家教导的,他一定是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后,认为利大于弊,才这样做的。在他看来,事业是第一位的,而个人的“操行”似乎已经放到了次要的位置。当然,他也有原则,那就是这样做的目的决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整顿军务和加强国防。这从他写过“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和从广东被罢官后两袖清风回故里又穷困潦倒至死的结局,可以证明。
由此看来,“书生气”虽然可敬可佩,但往往脱离客观条件,难以实现,对事业并无太大的好处;倒不如灵活一点,实事求是,审时度势,见机行事,倒可能对事业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