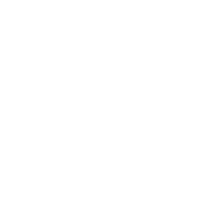·闽人要籍百部评鉴·
15.胡安国与《春秋传》
胡安国以二程的私淑弟子自居,成为理学的坚定信奉者。与其子侄辈胡寅、胡宁、胡宏、胡宪,均为南宋理学家,被称为“胡氏五贤”。胡安国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著作,就是《春秋传》三十卷。经世济民,感于时事,借《春秋》寓意,不拘章句训诂,成为宋代理学家以义理治《春秋》的代表作。南宋时期,胡安国《春秋传》被定为经筵读本,成了官学。入元后,科举于《春秋》经,规定以胡安国的《春秋传》定经文,与《春秋》三传并行。由此可见,胡安国的《春秋传》影响了几百年的《春秋》学研究与众多的读书士子。
《春秋传》三十卷,(宋)胡安国撰。
胡安国(1074—1138),字康侯,号青山,学者称武夷先生,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人。北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进士,为太学博士,旋提举湖南、成都学事,以不肯附权贵,为蔡京、耿南仲所恶。南宋高宗即位后,拜胡安国为给事中,后又拜为中书舍人兼侍讲。胡安国上《时政论》二十一篇,力陈中兴恢复之策略。后以反对重用朱胜非而去职。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拜胡安国为徽猷阁待制、知永州,胡安国辞不就,诏以经筵旧臣,重闵劳之,特从其请,提举江州太平观,令纂修所著《春秋传》。书成,高宗谓深得圣人之旨。诏命复提举太平观,进宝文阁直学士。绍兴八年(1138)卒,享年六十五。朝廷赐谥“文定”,故后世尊称其为胡文定公。
胡安国与程颢、程颐弟子谢良佐、杨时、游酢等人义兼师友。在太学学习期间,又从程颐之友朱长文、靳裁之,接受了程颐、程颢的学说,以二程的私淑弟子自居,成为理学的坚定信奉者,极力推崇二程是孔孟之道的直接继承人。《宋元学案》中专门为胡安国立《武夷学案》,评价其为“私淑洛学而大成者”。《宋元学案》评论说:“南渡昌明洛学之功,文定几侔于龟山,盖晦翁(朱熹)、南轩(张栻)、东莱(吕祖谦)皆其再传也。”胡安国及其子侄辈胡寅、胡宁、胡宏、胡宪,均为南宋理学家,被称为“胡氏五贤”,清人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三云:“胡氏父子叔侄阐发经旨,绍述儒学,世以五贤并称。”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冬,胡安国为躲避战乱,携带家眷到湖南湘潭,隐居在碧泉,并以住宅为书堂,著述《春秋传》并教授子弟生徒,除自己的子侄胡寅、胡宏、胡宪等外,还吸引了众多湖湘士子前来就学,从游弟子数十人。胡安国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理学派别——湖湘学派的实际创始人。湖湘学派研究传统理学,提倡修身为学,主张经世致用,重教化,讲名节,轻利禄,憎邪恶,对湘潭乃至湖南的人文教化和道德风尚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史》(卷四百三十五,列传第一百九十四)胡安国本传记载,“有文集十五卷,《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一百卷”,今已亡佚。胡安国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著作,就是《春秋传》三十卷。
《春秋》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两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作为儒家经典,据传是由孔子根据鲁国史书修订而成,而孔子修《春秋》,蕴涵着他的深刻政治、伦理、文化思想,“笔寓褒贬”中体现出了“春秋大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是阐释经义的著作。出于对儒家经典的尊崇,本着阐释圣人思想的热忱,胡安国毕生致力于《春秋》学的研究和著述,可谓披肝沥胆,呕心沥血。他从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开始,直至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底,历时三十余年,完成了在历史上享有盛誉的《春秋传》三十卷,共十余万字。《宋元学案》引录胡安国语,曰:“某初学《春秋》,用功十年,遍览诸家,欲求博取,以会要妙,然但得其糟粕耳。又十年,时有省发,遂集众传,附以己说,犹未敢以为得也。又五年,去者或取,取者或去;己说之不可于心者,尚多有之。又五年,书成,旧说之得存者寡矣。及此二年,所习似益察,所造似益深,乃知圣人之旨益无穷,信非言论所能尽也。”《四库全书总目·春秋传》中提到,“俞文豹《吹剑录》称其自草创至於成书,初稿不留一字,其用意亦勤矣。”
胡安国《春秋传》的体例,颇具特色。从汉代开始,《春秋》学的研究传统,是就或《公羊传》、或《谷梁传》、或《左传》的三传之一来进行阐释,从中唐啖助、赵匡、陆淳之后,许多唐、宋学者对三传的看法有所改变,从而使解经方法也随之而变,往往从专主一传,变而为弃传从经,兼采三传。胡安国对《春秋》三传都有很深的研究,他的《春秋传》,采取“事取左氏,义兼公谷”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兼采三传。他继承了传统的以义例解经的方法,但又有所创新;他也继承董仲舒“从变从义”的方法,于不同的史实之中解读出全新的经义;他同时还兼取百家之说,成一家之言,其经义具有明显的时代意义,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春秋》学史上,有“《春秋》经说”和“《春秋》史说”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春秋》经说”以为经所记之史实阐发儒家“王道”政治的观念,而“《春秋》史说”则以为《春秋》为信史而非经,没有所谓的微言大义。相应地,在解经方法上,“《春秋》经说”重在发掘其微言大义并以义例解经,也用灵活的从变从义的方法解经;持“《春秋》史说”观点的,则更侧重用史事来解读经典。胡安国的对《春秋》这一经典的认识,在《春秋》之“经”与“史”之间,采取了兼取的立场。一方面,他认为《春秋》所记是史实,同时他又认为圣人是“以鲁史而见王法”,亦即“《春秋》立文兼述作”(隐公元年胡氏传),乃“史外传心之要典”。这是胡安国所持的寓经于史、经史一体的《春秋》观。
胡安国的《春秋传》,作于宋室南渡之际,完成并表进于南渡之后,这一时代背景,对该书的写作必然产生直接的影响,这也就是《四库全书总目》所说的“故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于《经》旨”。胡安国也自谓其著书之目的,在于“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大法略具”。
胡安国《春秋传》中所阐发的大义,首先是“尊王”的思想观念。“尊王”,是《春秋》学的传统,胡安国《春秋传》蕴涵着丰富的尊王思想,是宋代《春秋》学的突出代表。其“尊王大义”既是对传统的继承,又为这个传统之流注入新的内涵。胡安国为宋代加强皇权与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服务,阐发了“《春秋》尊君抑臣”、“尊天子抑制诸侯”的经义,其尊王之义的背后,是宋儒重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大一统”秩序的愿望。胡安国对“隐公元年春王正月”的阐释,就反复强调大一统。他说:“元年,即位之一年也。必号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则与天地参。故体元者,人主之职。”这里所谓“体元”就是强调慎始,强调定于一。他又说:“王正月。……加王于正月者,公羊言大一统是也。”“谓正月为王正,则知天下之定于一也。”所谓“定于一”,从政治的角度讲,就是大一统,就是“土无二王”,就是“尊无二上”。胡安国虽然“尊王”,但并不主张“绝对君权”,他继承伊川之说,既尊王权,更尊王道,亦即遵循天理,并以此来制约王权。他期盼君主能秉持“天地之性”,成为“圣王合一”式的理想统治者,这就是他“尊王”并“崇道”的最终目的。
胡安国《春秋传》中,以“崇道”的思想,对传统天命论、灾异论等制约君权思想进行扬弃。《春秋》灾异说,是传统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看似牵强附会,荒诞不经,不过其本意乃在于以天变警戒、制约王权。胡安国承《春秋》各家之学,颇重灾异之说。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和啖赵学派的“举王纲、正君则”大义也对《胡传》产生了重要影响。胡安国重视天人感应,认为灾异是由人君失德、失政所致,人君若不能修德,则必有国亡身弑之祸,从而要使人君“鉴观天人之理”,有“恐惧祗肃之意”;同时,他也认为可以做到“以人胜天,以德消变”。胡安国的灾异之说在系统性上不及公羊,但也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重视灾变而重民命,强调人主分灾救患之职。宋代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民本”思潮比较活跃,在《春秋传》中,胡安国认为,王道政治的立国理念是“国以民为本”,王道的政治境界即是“与民同忧乐”,其治民原则在于“使民以时”、“不竭民力”,他把恤民固本作为政治的根本性问题来加以强调。
胡安国《春秋传》还强调“正人伦”的意义。如,胡安国于《庄公二十年》曰:“礼义,天下之大防也。”于《文公十六年》曰:“三纲,人道之大伦,君臣之义不可废。”于《昭公十一年》,曰:“三纲,军政之大本。君执此以御其下,臣执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于是乎在。”于《僖公十六年》曰:“谨夫妇之道,正人伦之统,明王教之始。”……在《春秋传》中,胡安国“正人伦”的观点还可以举出很多。“正人伦”的观点是儒家的传统观点,而胡安国在两宋理学日趋兴盛的大背景下提出这一观点的,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天理”与“人欲”联系对比,进行剖析和阐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与两宋之际金人入侵中原、北宋覆灭、南宋偏安的历史时代密切相关,胡安国在《春秋传》中,彰显出了严夷夏之防、诛讨乱臣贼子的问题。从《春秋传序》中,从书成以后胡安国的进表中,可以看出:谨夷夏之辨、严夷夏之防,尊王攘夷、以夏变夷,是胡安国《春秋传》的所谓“大法”,亦即撰书的主要宗旨之一。《春秋传》于《僖公二十三年》曰:“《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尤谨于华夷之辨。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以礼义也,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人类灭矣。……夷不乱华,成公变之,贬而称子,存诸夏也。”于《宣公十一年》曰:“经之大法,在诛乱臣,讨贼子。有乱臣则无君,有贼子则无父。无父与君,则中国变为夷狄,人类殄为禽兽,虽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胡安国继承传统夷夏观,以礼义为夷夏之辨的标准。但由于身处国家危亡之际,所以胡安国更强调攘夷,并突出公羊“大复仇”大义,力主加强武备,恢复中原。
胡安国志在经世济民,感于时事,往往借《春秋》寓意,不拘章句训诂,成为宋代理学家以义理治《春秋》的代表作。《朱子语录》谓“胡氏《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此论被《四库全书总目》称作“千古之定评也”。
南宋时期,胡安国《春秋传》被定为经筵读本,成了官学。入元后,元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下诏实行科举,于《春秋》经,规定以胡安国的《春秋传》定经文,与《春秋》三传并行。《四库全书总目·春秋传》曰:“明初定科举之制,大略承元旧式,宗法程、朱。而程子《春秋传》仅成二卷,阙略太甚。朱子亦无成书。以安国之学出程氏,张洽之学出朱氏,故《春秋》定用二家。盖重其渊源,不必定以其书也。后洽《传》渐不行用,遂独用安国书。渐乃弃《经》不读,惟以安国之《传》为主。当时所谓经义者,实安国之传义而已。”可见,胡安国的《春秋传》影响了几百年的《春秋》学研究与众多的读书士子。
胡安国《春秋传》传本较多,宋刊本今较罕见,明代有湖广两地刻本,崇道堂刻本,明正统十二年(1447)刊《六经》本,内府刊《六经》本等,清代有《四库全书》本。现代出版的,则有上海书店1984年出版的《四部丛刊续编》本,巴蜀书社1984年出版的《胡氏春秋传》,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出版的《胡氏春秋传》(摛藻堂四库荟要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