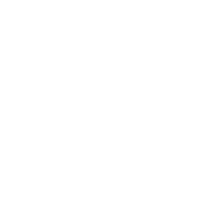·闽人要籍百部评鉴·
5.谭峭与《化书》
谭峭是唐末五代时期道教的代表人物之一。虽出身官宦,然少小即绝意仕进,雅好黄老、诸子之学。师于嵩山道士十余年,归炼泉州清源紫泽洞。虽以学道自隐,但十分关心世道治乱与民生疾苦。所著《化书》上承道家根本,下开内丹之学,是道教理论的一次重要发展,在中国道教思想史上占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全书“文词简畅,义理粲然。其中虽有长生、太上等语,而无龙虎刀圭伪妄之术、恍惚之语”。其治国经世之思想,更是在道教思想家中个性凸显的闪光点。
《化书》六卷,(五代)谭峭著。
谭峭(生卒年不详),字景升,道号紫霄真人,唐末五代时期道教的代表人物之一。明代何乔远在《闽书》卷七《方域志》关于清源山的记录中有载:“紫霄,名峭,字景升,本州人,唐国子司业洙之子。” 清源山原在福建泉州境内,谓之“本州人”,当为泉州人。清人吴任臣《十国春秋·谭紫霄传》亦称:“谭紫霄,泉州人也。”谭峭生逢乱世,自幼聪颖,虽出身官宦之家,少小即被其父训以进士为业,但一直雅好黄老、诸子之学,常披阅神仙传记,最终以游历终南山为借口,辞父学仙,一去不返。师于嵩山道士十余年,得辟谷养气之数。尝醉游,夏作乌裘, 冬衣葛衫, 或卧霜雪中。又云游天下道教名山,入南岳炼丹。南唐后主李煜曾召至建康,赐号“紫霄真人”,又授其“金门羽客”,颁赐紫金阶和大量财产,他拒而不受。复归泉州后,修炼于清源紫泽洞。谭峭曾自云得张道陵《天心正法》,闽王王延钧奉为“正一先生”。谭峭虽以学道自隐,但十分关心世道治乱、民生疾苦。约在宋开宝年间无疾而终。
谭峭著有《化书》六卷,凡一百一十篇。书成之后,求南唐大臣宋齐丘为序,齐丘遂夺为己有而序之,题名《齐丘子》。后经陈抟揭露,始得纠正。全书篇章依次为:“道化”“术化”“德化”“仁化”“食化”“俭化”。其中“道化”卷论修道原理,“术化”卷论修行法术原理,其余四卷则论治国原理。《化书》内容较为驳杂,或祖黄老,或本儒释,宋人陈振孙《郡斋读书志》和清《四库全书总目》都将其列入杂家类,但就其主要思想而言,当属道教的著作。此外,书中又用大量篇幅论述了社会的发展演化,揭示兴衰治乱的原因,进而提出治国的对策。
《化书》开宗明义,第一篇便道出了全书的宗旨:“道之委也,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生而万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气,气化神,神化虚,虚明而万物所以通也。是以古圣人穷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养气,忘气以养神,忘神以养虚。虚实相通,是谓大同。”(《化书·道化》)在此之后,不论是讲修道,论治国,还是谈自然之化,都是从这个宗旨而来,皆不离这个宗旨。因此,其内容虽涉及修道、法术和治国原理,但其理论实质仍应归结为道教的内丹之学。如果不了解这一点,而是只盯着字面,专以其他末端为宗,皆不免于舍本逐末,不得其神。除此之外,谭峭还取“道法自然”之意,从自然万物和社会现象出发释道,并以“道”论治国,以治国喻“道”,同情广大人民的的悲惨遭遇,揭露统治者的无情剥削和奢侈无度,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的建议,以期君民之间能够共利互助,损有余而补不足,社会无为而治,进而回归到原始的自然状态。
该书卷一《死生》篇指出,世界起源于“虚”,“虚化神,神化气,气化血,血化形”,进而生成万物,最后又死而复归于“虚”。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万物非欲生,不得不生;万物非欲死,不得不死”,可见天地万物的生灭变化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卷二《动静》篇则进一步将天地万物生成、演化的原因归结为阴阳两种对立因素的相互作用。所谓“动静相磨,所以化火也;燥湿相蒸,所以化水也;水火相勃,所以化云也;汤盎投井,所以化雹也;饮水雨日,所以化虹霓也”。谭峭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化书》,表明“化”的哲学范畴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据最核心的地位。
谭峭一生经历了唐末、五代、宋初三个战祸绵延、动荡不安的时代。他在云游四海的过程中,目睹了民众的悲惨遭遇,深知民间的疾苦,并能指出民众的苦难源于统治者剥削太重,“王者夺其一,卿士夺其一,兵吏夺其一,战伐夺其一,工艺夺其一,商贾夺其一,道释之族夺其一”。(《食化·七夺》)农民除了经常遭受上述“七夺”之外,丰年的谷价低,用钱交税,又遭到一次剥夺;荒年的收成减少,更是要遭到剥夺。所谓“稔亦夺其一,俭亦夺其一,所以蚕告终而缲葛苎之衣,稼云毕而饭橡栎之实”。(《食化·七夺》)由于统治者采取欺罔、鞭挞、掠夺、刑戮等手段对待民众,使得“民腹常馁,民情常迫”,不得不被迫铤而走险,结果是“天子作弓矢以威天下,天下盗弓矢以侮天子。君子作礼乐以防小人,小人盗礼乐以僭君子。有国者好聚敛,蓄粟帛、具甲兵以御贼盗,贼盗擅甲兵、踞粟帛以夺其国”。(《德化·弓矢》)
关于治国之道,儒道两家向来意见相左。道家讲究“无为而治”,而儒家则强调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制度下,以道德仁义、礼义刑罚来治国。在《化书》中,谭峭却能吸收儒家的观点,将五行相生相克与儒家讲的仁、义、礼、智、信五常结合起来,提出“道德者,天地也。五常者,五行也。仁,发生之谓也,故君于木。义,救难之谓也,故君于金。礼,明白之谓也,故君于火。智,变通之谓也,故君于水。信,慤然之谓也,故君于土。仁不足则义济之,金伐木也。义不足则礼济之,火伐金也。礼不足则智济之,水伐火也。智不足则信济之,土伐水也。始则五常相济之业,终则五常相伐之道,斯大化之性也”。(《仁化·五行》)但谭峭又以儒家所说的五常太过繁琐,容易使人们无所适从,认为不如将其归之为“一”,以达到“忘其名则得其理,忘其理则得其情,然后牧之以清静,栖之以杳冥,使混我神气,符我心灵”(《德化·五常》)的境界。谭峭还进一步将人与动物进行对比,指出禽兽亦“有巢穴之居,有夫妇之配,有父子之性,有死生之情。乌反哺,仁也;隼悯胎,义也;蜂有君,礼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反而是自诩为民众的教导者和仁义礼智信化身的统治者“教之为纲罟,使之务畋渔。且夫焚其巢穴,非仁也;夺其亲爱,非义也;以斯为享,非礼也;教民残暴,非智也;使万物怀疑,非信也。膻臭之欲不止,杀害之机不已”。(《仁化·畋渔》)
显然,作为道教理论家的谭峭,站在道教哲学的立场上,还是认为儒家的道德、仁义、刑礼的作用有限,不得要领,并不能真正解决治国的问题。所谓“道德有所不实,仁义有所不至,刑礼有所不足,是教民为奸诈,使民为淫邪,化民为悖逆,趋民为盗贼。上昏昏然不知其弊,下恍恍然不知其病”,(《道化·大化》)最终只能像“醉者负醉,疥者疗疥”一样,“其势弥颠,其病弥笃,而无反者也”。(《道化·稚子》)因此,谭峭指出,要解决治国中的根本问题,还是要靠行大“道”。因为“道”才是万物的根本,儒家所谓的仁义礼智信“五常”都是从“道”中生发出来的,是“道”的一种退步,故治国必须循用道化的法则,通过“忘”的办法,逆而化之,使“五常”重新回复于“道”,以达到“无亲无疏无爱无恶”的“大和”社会。
另一方面,谭峭又从现实的物质生活出发,提出了“食为五常之本,五常为食之末”的观点,将“食”作为伦理道德的基础与社会秩序的保障,要求统治者首先满足民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故曰:“君无食必不仁,臣无食必不义,士无食必不礼,民无食必不智,万类无食必不信。……苟王者能均其衣,能让其食,则黔黎相悦,仁之至也;父子相爱,义之至也;饥饱相让,礼之至也;进退相得,智之至也;许诺相从,信之至也。教之善也在于食,教之不善也在于食。其物甚卑,其用甚尊,其名尤细,其化尤大,是谓无价之货。”(《食化·鸱鸢》)
鉴于“食”对国家治乱的重要性,以及当时贫富悬殊的社会状况,谭峭提出了“均食”、“行俭”的主张。他说:“俭者,均食之道也。食均则仁义生,仁义生则礼乐序,礼乐序则民不怨,民不怨则神不怒,太平之业也”,(《俭化·太平》)“能均其食者,天下可以治”,(《食化·奢僭》)“一人知俭则一家富,王者知俭则天下富”。(《俭化·悭号》)由于一定时期内的物质财富总量有限,要想天下太平,防止天怒人怨,统治者就必须做到平均分配,厉行节俭,以此来维系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在此意义上,谭峭也将“俭”作为五常之本。“夫仁不俭,有不仁;义不俭,有不义;礼不俭,有非礼;智不俭,有无智;信不俭,有不信。所以知俭为五常之本,五常为俭之末。”(《俭化·损益》)因为有俭的约束,才能使五常之道长存不坠,民生日用皆有所本。“所以议守一之道,莫过乎俭。俭之所律,则仁不荡,义不乱,礼不奢,智不变,信不惑。故心有所主,而用有所本,而民有所赖。”(《俭化·御一》)当然,谭峭所说的“俭”范围很广,不仅指理财,还包括养生、修道、为政等各方面内容。“俭于听可以养虚,俭于视可以养神,俭于言可以养气,俭于私可以获富,俭于公可以保贵,俭于门闼可以无盗贼,俭于环卫可以无叛乱,俭于职官可以无奸佞,俭于嫔嫱可以保寿命,俭于心可以出生死,是知俭可以为万化之柄。”(《俭化·化柄》)
谭峭在提出治国的原则之后,并未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而是进一步探讨了治国中应当采取的种种具体方法。他认为,治国不仅要有“道”,还要有正确的“术”。如果在“道”的指导下,运用合理的“术”治国,就像“转万斛之舟者,由一寻之木;发千钧之弩者,由一寸之机”一样,“一目可以观大天,一人可以君兆民”,(《术化·转舟》)从而实现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反之,如果在治国的过程中不重视“术”,只是空谈义理,就会出现“仁义者常行之道,行之不得其术以至于亡国;忠信者常用之道,用之不得其术以至于获罪;廉洁者常守之道,守之不得其术以至于暴民;财辩者常御之道,御之不得其术以至于罹祸”(《德化·常道》)的恶果。
至于“术”的使用,谭峭从道家的基本理论出发,提出:一要慎施恩赏。因为恩赏虽可激励部下,但无度的恩赏却可能适得其反。“侯者人所贵,金者人所重,众人封公而得侯者不美,众人分玉而得金者不乐。是故赏不可妄行,恩不可妄施。其当也,犹为争夺之渐;其不当也,即为乱亡之基。故我自卑则赏不能大,我自俭则恩不得奇。观乱亡之史,皆骄侈恩赏之所以为也。”(《德化·恩赏》)二要施恩勿望报,虽不望报,自然有报。“救物而称义者,人不义之;行惠而求报者,人不报之。民之情也,让之则多,争之则少;就之则去,避之则来;与之则轻,惜之则夺。是故大义无状,大恩无象。”(《仁化·救物》)三要正确处理得与失的关系,有容人之量,无疑人之意。“抑人者人抑之,容人者人容之,贷其死者乐其死,贷其输者乐其输。所以民盗君之德,君盗民之力,能知反复之道者,可以居兆民之职。”(《德化·酒醴》)四要与民众疾痛相关,同甘共苦。“心相通而后神相通,神相通而后气相通,气相通而后形相通。故我病则众病,我痛则众痛,怨何由起,叛何由始?”(《仁化·蝼蚁》)
总之,在谭峭看来,社会的矛盾和动乱都是由于统治者的“有为”造成的,“民不怨火而怨使之禁火,民不怨盗而怨使之防盗”,(《德化·养民》)“非兔狡,猎狡也;非民诈,吏诈也。慎勿怨盗贼,盗贼惟我召;慎勿怨叛乱,叛乱禀我教。不有和睦,焉得仇雠;不有赏动,焉得斗争”。(《仁化·大和》)因此,根本上还应行“无为”之术,“济民不如不济,爱民不如不爱……夫禁民火不如禁心火,防人盗不如防我盗,其养民也如是”,(《德化·养民》)“心不可伏,而伏之愈乱;民不可理,而理之愈怨。水易动而自清,民易变而自平”。(《仁化·止斗》)只有顺天应时,谨守“无为”之道,“不逆万物之情”,“夺其机,藏其微,羽符至怪,阴液甚奇”,才“可以守国,可以救时,可以坐为帝王之师”。(《术化·帝师》)
后世学者对谭峭的《化书》一直有着很高的评价。如明人谢肇淛就说过:“谭景升《化书》一百一十篇,文词简畅,义理粲然。其中虽有长生、太上等语,而无龙虎刀圭伪妄之术、恍惚之语,《道德》、《南华》之后,此其翘然者也。”(《文海披沙》卷四)。
《化书》的刊本存世颇多。早在宋代就有刊刻,后编入《道藏》;元代有秦升家塾刊本;明清时期主要有:明天顺年间王府本、明弘治十七年(1504)刘达翻刻本、明正统年间《道藏》本、《宝颜堂秘笈》《四库全书》《墨海金壶》《榕园丛书》《说郛》等刊本。199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丁祯彦、李似珍点校本《化书》,可便读者阅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