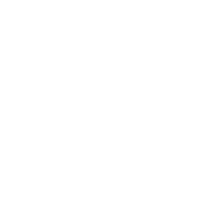·“第二届福文化论坛”专题·
朱子理欲观与幸福观刍议
方彦寿
“明天理、灭人欲”是朱子理学伦理思想的核心理念。所谓明天理,即明辨天理、人欲之别,时刻保存天理于人心之中,并恢复被人欲遮蔽的天理,遵循天理,循理而行。所谓“灭人欲”,朱子往往也称之为去人欲、遏人欲或克人欲。他说:“要紧只在克字上,克者,胜也。日用之间,只要胜得他,天理才胜,私欲便消;私欲才长,天理便被遮了。要紧最是胜得去,始得。”[1]
朱子的幸福观,则渊源于他对《洪范九畴》的解读。一方面,朱子从限制君权,为皇权立标准来解读九畴中的“皇极”;认为福泽天下、福润苍生,是检验人君治理天下得失成败的关键,从而将皇极与造福万民的儒家民本思想和幸福观紧密地结合起来。同时,此举对唐代经学家孔颖达把“皇极”解读为“大中”,视为“施政教,治下民”的“大中之道”[2],产生了颠覆性的效果。
何为天理?何为人欲?朱子曾从公私、正邪、善恶这三个方面对其以天理为核心的理欲观进行了论证,从中可以得出三点结论,即天理为公、人欲为私;天理为正,人欲为邪;天理为善,人欲为恶。[3]
那么,朱子的理欲观与幸福观又有何内在联系?朱子曾通过读史,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如西汉游侠郭解,事载《史记·游侠列传》《汉书·游侠传》等。其人生,既有早年犯奸作科、抢劫盗窃、私铸钱币、盗挖坟墓、草率杀人的一面,也有后期检点约束自我,以恩报怨的一面,但其最终落得族诛的下场。班固称其“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4]朱子在编纂《资治通鉴纲目》一书评价郭解的行为时,转引了班固的话,并强调说:“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5]在《答蔡季通》书信中说:“昨日读《通鉴》,至班固论郭解,有温良泛爱绝异之资而不入于道德,以至于杀身亡宗处,方为之掩卷太息,以为天理人欲之间毫厘一差,其为祸福之不同乃至于此。”[6]此言是说,人生的福与祸,与行为个体自身的行为举止有关,而行为举止的取舍,受其内在的价值观——对天理与人欲的认知的支配。是与非、对与错,以及福与祸的抉择,往往就在其毫厘之间。正因如此,朱子对《左传》的历史观就颇有非议。认为“《左传》只道得祸福利害底说话,于义理上全然理会不得。”[7]
由此可知,朱子是要以其明公理、明正理、明善理的理欲观和义利观,由“义理”着手来节制和规范个人的物质需求和欲望,在祸福利害的抉择中,使用正确的道德理念立德行善,为天下苍生造福和谋利,为民众袪祸和避害。
一、“明公理,灭私欲”与幸福观
“明公理,灭私欲”是朱子理欲观的重要内涵之一。
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朱子强调一个“仁”字,在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上,朱子则主张一个“公”字。他认为,“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8]
存心以公,而非以私,此为朱子的处世之道。他把“公”看成是“仁”的基本要素,是达到“仁”的方法,认为“仁则公,公则通,天下只是一个道理。不仁则是私意,故变诈百出而不一也。”[9]
对集天下公权,同时也集万家之福于一身的君王,朱子提出了特别的要求。
一是“建极”,“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动之发,无不极其义理之当然,而无一毫过不及之差,则极建矣。”[10]极是标准,建极,就是要求君王以儒家“义理”思想正心修身,“明公理,灭私欲”无毫厘之差,其行为方可成为天下的根本标准。[11]
二是“敷福”。延续其师朱子的思想,朱门高弟蔡沈认为,“极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于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与庶民。”[12]君王不应借天下公权,将天下之福“厚”其一身,而应将此福祉普施天下万众庶民。这体现的是天理之公。
即以人君的福寿而言,同样也受制于其个人的品德高下。朱子门人潘时举以《诗经·天保》请教先生,所涉及的内容有福与寿。《诗经·天保》原诗如下:
天保定尔,亦孔之固。俾尔单厚,何福不除?俾尔多益,以莫不庶。
天保定尔,俾尔戬穀。罄无不宜,受天百禄。降尔遐福,维日不足。
天保定尔,以莫不兴。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吉蠲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尝,于公先王。君曰卜尔,万寿无疆。
神之吊矣,诒尔多福。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群黎百姓,遍为尔德。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13]
针对以上内容,潘时举问:“(《天保》)第一章至第三章,皆人臣颂祝其君之言。然辞繁而不杀者,以其爱君之心无已也。至四章则以祭祀先公为言,五章则以‘遍为尔德’为言。盖谓人君之德,必上无愧于祖考,下无愧于斯民。然后福禄愈远而愈新也。故末章终之以‘无不尔或承’。”对潘时举的说法,文末以“先生颔之”作结,即朱子对潘时举的说法表示赞同。其时在场的弟子有董铢(叔重),他以《诗经·蓼萧》问:“令德寿岂,亦是此意。盖人君必有此德,而后可以称是福也。”[14]朱子于此也作了答复,肯定了无论是福还是寿,都必须与其德相匹配。此为朱子的德福观、德寿观。
在解读《诗经·卷阿》诗时,朱子与其弟子认为,“诗中凡称颂人君之寿考福禄者,必归于得人之盛。”“人君所以致福禄者,未有不自得人始也。”[15]此所谓得人,指的显然是用人得当,所得之人均为具有公正之心的贤才或能人。
君王如此,大臣更应效法。他说:“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16]他还借已故名相陈俊卿的话说,“此钩党之渐,非国家之福也。愿诏大臣,一以大公至正为心,并用恩仇,兼忘物我,唯才是任,毋恤其它,则植坏群散而人人得以自效矣。”[17]朝中大臣为追逐一己私利而拉帮结派,显然对国家、对民众均非福音,只会祸国殃民。
公正无私,将家国安危系于一身,却将自身的祸福置之度外,这是朱子对先贤李纲的赞美。他说:“李公之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祸福,虽以谗间窜斥,屡濒九死,而其爱君忧国之志终有不可得而夺者,是亦可谓一世之伟人矣。”[18]
对普通士人来说,公和仁也是做人的基本要求。他说:“盖人撑起这公作骨子,则无私心而仁矣。盖公只是一个公理,仁是人心本仁。人而不公,则害夫仁。故必体此公在人身上,以为之体,则无所害其仁,而仁流行矣。”[19]
对乡村最基层的村民而言,朱子也提出了“和睦乡邻,救恤灾患,输纳苗税,畏惧公法”[20]的基本要求。
二、“明正理,灭邪欲”与幸福观
在辨析明公理灭私欲的基础上,朱子还提出了“明正理,灭邪欲”的理念。他认为“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21]除了肯定公理为正,私欲为邪之外, 朱子还以“义”的道德原则来衡量和区分正邪。他说:“义者,宜也,乃天理之当行,无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22]这段话,是对孟子“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的解读。朱子认为,所谓人之安宅,“在人则为本心全体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无人欲陷溺之危。人当常在其中,而不可须臾离者也,故曰安宅。”[23]在朱子看来,义是公义,是正义之道,也就是符合天理的“正道”;利是私利,毫无疑问,是违背正理的邪欲。
衡量是正还是邪,除了公与私、仁与义标准之外,是否合宜、是否得当,也是评判正与邪的标准之一。朱子曾以父母慈爱子女为例说:“父母爱其子,正也;爱之无穷而必欲其如何,则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间,正当审决。”[24]]朱子认为,父母爱其子女,这是符合天理的正常行为,是正理,若流于溺爱,则是人欲,所以在《家训》中,朱子提出“子孙不可不教”。父母在对子女施予“慈”爱的同时,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教其做人的道理,知礼仪,尽孝道。将这一思想与福文化相结合,就引出了端正家风的话题。也就是说,提倡孝道,端正家风,营造好的家风,能让子孙福泽绵延,坏的家风则必然祸及子孙。
他以上古时期的几位圣君为例,阐释其后裔子孙得其祖上福荫之佑时说:“殷汤、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贤,讲论道义,无有过差,又举贤才,遵法度而无偏颇,故能获神人之助,子孙蒙其福祐。”[25]“畏天敬贤,讲论道义”“举贤才,遵法度”,此为上古时期的帝王家风。朱子希望以此能影响南宋时期的帝王家风。
通过对朱子以上的观点的辨析,可以得出“明正理,灭邪欲” 也是朱子理欲观重要的内涵之一。
“明正理,灭邪欲”与幸福观的关系,首先突出表现在明正理用正人天下蒙其福,反之亦然。朱子说:“公明正大之人用于世,则天下蒙其福;私暗邪僻之人得其志,则天下受其祸。此理之必然也。”[26]秉持这一理念,朱子将此运用在“正君心、除邪佞”的帝王之学中。希望帝王能成为“公明正大之人”,也希望他所任用的大臣都是“公明正大之人”。这样,天下百姓才能“蒙其福”。
淳熙十五年(1188)十一月所上《戊申封事》中,朱子把“选任大臣”列为今日之急务之一。他认为,辅佐帝王处理天下大事,“必得刚明公正之人而后任”,而当今朝廷“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窃位者,”其原因何在?就在于孝宗一味宠信宫廷近习,“彼以人臣窃国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发其奸也”,故专门选择如秦桧那样的奸臣“以塞贤路,蔽主心”。所以,他希望宋孝宗在选任大臣上,能够“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适吾意,而求其能辅吾德;不忧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为燕私近习一时之计,而为宗社生灵万世无穷之计。”[27]宗社,指的是国家社稷;生灵,指亿万民众。是“刚明公正之人”肩负重任,还是让“鄙夫窃位”,直接关系到宗社生灵、国家民众的万世长远的幸福与否。
在《戊申封事》中,朱子将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运用到对人君的劝谏中,提出了“邪正之验著于外者,莫先于家人而次及于左右,然后有以达于朝廷而及于天下焉。”[28]
所谓“家人”,对帝王而言,首先是“宫闱之内,端庄齐肃”,使“后妃有关雎之德”,“无一人敢恃恩私以乱典常,纳贿赂而行请谒,此则家之正也。”所谓“左右”,指的是“贵戚近臣”。“无一人敢通内外、窃威福,招权市宠,以紊朝政,此则左右之正也。”最后,将此推至“内自禁省,外彻朝廷,二者之间洞然,无有毫发私邪之间,然后发号施令,群听不疑,进贤退奸,众志咸服。”[29]从而达到正天下的目的。
朱子在从政中,坚持“治吏以严”“御吏以法”,才能为民除害,从而保护善者弱者。对官吏的基本要求,朱子认为“大抵守官,只要律己公廉,执事勤谨,昼夜孜孜,如临渊谷,便自无他患害。”[30]公、廉、勤、谨(公平公正,廉政勤政,谦恭谨慎),此即朱子制定的为官基本守则。其中的“廉”字,他认为是对为官者最基本的要求。他说:“仕宦只是廉勤自守,进退迟速自有时节,切不可起妄念也。……到官凡百以廉勤爱民为心乃佳。”[31]不可起妄念,指的即不可萌生贪念,而要坚守廉洁的底线,一心勤政爱民。
朱子对奸佞误国、贪腐害国的危害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对官场腐败深恶痛绝。他谴责当时的官场,“盖通身是病,无下药处”。他希望有这么一位大贤君子,能“正其根本,使万目俱举,吾民得乐其生耶!”[32]根本不正,则为民造福就成了一句空话!所以,在朝时,他力劝君主正心诚意远离奸邪;在地方,则打击贪官污吏,反贪倡廉。在给弟子传授为宦之道时,他强调“当官廉谨”“事上以礼,接物以诚,临民以宽,御吏以法”。[33]
针对时政的各种弊端,朱子还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张,如除奸佞、正吏治等。而反贪倡廉,是其为政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政治主张,实际上是朱子“存正理、灭邪欲”的理学思想在其为政之道的反映,也是其以民为本为民造福思想的重要手段。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八月,朱子生平首上封事,就对贪佞当道的现象提出严厉批评。他认为,地方官是否贤良,是否清廉,直接关系到百姓的安危休戚,关系到百姓的民生福祉。而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的地方官之所以横行无忌,又与朝中佞臣密切相关。对此,朱子提出只有“以正朝廷为先务”,此弊病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此后的数十年间,朱子在上给朝廷的众多奏章中,几乎都离不开“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等内容。与此一脉相承的,则是他在各地从政时,大刀阔斧端正吏治,惩治腐败。诸如淳熙八年(1181)十二月在浙东救灾,依法查办、上状弹劾一批包括唐仲友在内的贪官污吏。
朱子惩治腐败、查处贪官的理念就是他所说的,“公明正大之人用于世,则天下蒙其福;私暗邪僻之人得其志,则天下受其祸。”[34]而惩治腐败、查处贪官,就是其清除祸国殃民的邪恶势力的举措。
三、“明善理,灭恶欲”与幸福观
“明善理,灭恶欲” 也是朱子理欲观重要的内涵之一。
他说:“善恶二字,便是天理、人欲之实体。今谓性非人欲可矣,由是而并谓性非天理,可乎?”[35]从本源上来说,天理是善的,而人欲则是恶的。人欲是潜藏在人心中为恶的一面,是一切违反“仁义礼智信”的不善行为的根源,它包括一切不正当的、违背道德的、以私害公的,危害国家、危害公众利益的一切欲望和行为。所以,朱子提出:“人贵剖判,心下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恶念去之。若义利,若善恶,若是非,毋使混淆不别于其心。辟如处一家之事,取善舍恶;又如处一国之事,取得舍失,处天下之事,进贤退不肖。蓄疑而不决者,其终不成。”[36]这就进一步将明善理、去恶念提升到如何正确处理家事、国事、天下事来认识。
“明善理,灭恶欲”与幸福观又是何种关系?儒学先贤曾子说:“人而好善,福虽未至,祸其远矣;人而不好善,祸虽未至,福其远矣。”[37]人如果乐于行善,福虽然没有到来,但已远离灾祸了;人如果不乐于行善,灾祸虽然没有到来,但与福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了。朱子继承了这一思想。他认为,“为善则福报,为恶则祸报,其应一一不差者,是其理必如此。抑气类相感自如此耶?善恶各以气类相感,而其应便是理合如此。”[38]文中所谓“理必如此”“理合如此”中的“理”,指的就是“明善理”之理,天理之理。
在朱子看来,明天理、灭人欲的功夫实际上就是扬善去恶的功夫。正如北宋名儒程颐所说:“教人者,养其善心,则恶自消。”[39]朱子继承了这一思想,他说:“学者工夫只求一个是。天下之理,不过是与非两端而已。从其是则为善,徇其非则为恶。事亲须是孝,不然,则非事亲之道;事君须是忠,不然,则非事君之道。凡事皆用审个是非,择其是而行之。圣人教人,谆谆不已,只是发明此理。”[40]
1、明善理行善举关键在于“行”
朱子认为,“扬善去恶”的关键在于“行”。他说:“善在那里,自家却去行他。行之久,则与自家为一;为一,则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我自我。”[41] “《书》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功夫全在行上。”他批评当时的一种社会不良风气说:“专做时文底人,他说的都是圣贤说话。且如说廉,他且会说得好;说义,他也会说得好。待他身做处,只自不廉,只自不义,缘他将许多话只是就纸上说。廉,是题目上合说廉;义,是题目上合说义,都不关自家身己些子事。”[42]明善去恶的关键在于“行之之实”,而不是停留在只知作口头或书面文章上,这是朱子一再强调的“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43]的道德实践意义。
2、明善理行善举而不望福报
对行善有福报的说法,前贤有不同的说法。孟子回答滕文公“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43]受到了宋人郑厚的批评。他认为,“吉人惟知为善而已,未尝望其报也。为善而望其报,是今世委巷溺浮图者之处心也。孟子劝滕文公,曰:‘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是心何心哉!”[44]对郑厚的说法,建阳余允文有《尊孟辨》予以反驳。他说:
善者福之,淫者祸之,天之道也。吉人为善固不望报,而天必报之以福。可以天道难信而不足信欤?孟子劝滕文公为善,谓后世子孙必有王者,非但告之以周家之事,是亦以天道告之也。[45]
对郑厚、余允文的说法,朱子作了点评,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说:
孟子言:“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初无望报之心也。“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乃为太王避狄而言。《易大传》曰“积善之家,必有馀庆”。《书》曰:“作善降之百祥,”亦岂望报乎?[46]
朱子此言,对孟子所说,从史实方面对郑厚作了一个驳正。同时,对行善不望其报的行为作了肯定。这在《跋程宰登瀛阁记》一文中,可以得到印证。他说:“予闻之,古之君子施而不望其报,祀而不祈其福,盖以为善为当然。而天人之间,应若影响者,自不容已也。”[47]
3、明善理行善政以福泽万民
从善恶的角度来看,朱子认为,天理是善的,人欲则是恶的。他说:“盖善者天理之本然,恶者人欲之邪妄。”[48] “是以天之为道,既福善而祸淫,又以赏罚之权寄之司牧,使之有以补助其祸福之所不及。然则为人君者,可不谨执其柄,而务有以奉承之哉。”[49]所谓“以赏罚之权寄之司牧,使之有以补助其祸福之所不及”,是说给行善者以福,给行恶者以祸,此为天之道。而具体的赏罚之权则在各级行政部门,以对天道“祸福之所不及”必须起到补充的作用。
当然,对执政者来说,所推行的法律、政策,并非可以随心所欲。其法应该是良法,其政应该是善政,其效果,必须是为民造福,福泽万民。朱子在《己酉拟上封事》中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他说:“臣闻天有显道,厥类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祸福,皆其自取。未有不为善而以謟祷得福者也,未有不为恶而以守正得祸者也。而况帝王之生,实受天命。以为郊庙社稷神人之主,苟能修德行政,康济兆民,则灾害之去,何待于禳?福禄之来,何待于祷?”[50]
“百祥”者,百福之谓。行善者,上天降之百祥;行不善者,上天降之百殃。此所谓“作善”,于常人来说,可能只是一件救穷济困、修桥铺路的善举,但对执政者而言,则可能就是修德行政,作善得福,康济天下亿兆民众的善政。其功效,正如朱子所言,要远远大于只是被动地祈福禄、禳灾害。
结 语
朱子的理欲观,可分为公私、正邪、善恶三个层面,由“义理”着手来节制和规范个人的物质需求和欲望,在祸福利害的抉择中,使用正确的道德理念立德行善,为天下苍生造福和趋利,为民众袪祸和避害。
对集天下公权和万家之福于一身的君王,朱子提出了“建极”和“敷福”的要求,将福普施天下万众庶民,以体现天理之公。朱子对奸佞误国、贪腐害国的危害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对官场腐败深恶痛绝。在朝时,他力劝君主正心诚意远离奸邪;在地方,则打击贪官污吏,反贪倡廉。针对时政的各种弊端,朱子还提出了除奸佞、正吏治一系列政治主张。这些主张,实际上是朱子以“存正理、灭邪欲”的理学思想在其为政之道的反映,也是其以民为本为民造福思想的重要手段。“明善理,灭恶欲”也是朱子理欲观重要的内涵之一。他认为,“为善则福报,为恶则祸报,其应一一不差者,是其理必如此。”作为一个真正的儒者来说,朱子认为,明善理行善举关键在于“行”,不应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对执政者来说,明善理行善政的目标应是施福于民且福泽万民。
(作者系福州理工学院朱子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注:
[1](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四十一,中华书局1986年,第1063页。
[2](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卷十一,钦定四库全书本,叶13A。
[3]参拙文《朱熹“明天理,灭人欲”当代价值新解》,《东南学术》2016年第3期。
[4](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699 页。
[5](宋)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卷四,《朱子全书》 第8册,第277页。
[6](宋)朱熹:《朱文公续集》卷二,第25册,第4672页。
[7](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二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52页。
[8](宋)朱熹《孟子集注·梁惠王章句上》,《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02页。
[9](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86页。
[10](宋)蔡沈:《书集传》卷四,《朱子全书外编》,第147--148页。
[11]陈来:《一破千古之惑”——朱子对<洪范>皇极说的解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3月第50卷第2期。
[12](宋)蔡沈:《书集传》卷四,《朱子全书外编》,第147--148页。
[13](宋)朱熹:《诗集传》卷九,《朱子全书》第1册,第550—551页。
[14](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一,第2119页。
[15](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一,第2132页。
[16](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十二,第2735页。
[17](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九十六《少师观文殿大学士致仕魏国公赠太师谥正献陈公行状》,第25册,第4456页
[18](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邵武军学丞相陇西李公祠记》,第24册第3782页。
[19](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五,中华书局1986年,第2454页。
[20](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别集》卷九《辛丑劝农文》,《朱子全书》第25册,第5001页。
[21](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三,中华书局1986年,第228页。
[22](宋)朱熹:《孟子·离娄章句上》卷七,《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 281页。
[23](宋)朱熹:《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卷三,《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39页。
[24](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五《答熊梦兆》,《朱子全书》第23册,第2624页。
[25](宋)朱熹:《楚辞集注》卷一,《朱子全书》第19册,第31页。
[26](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金华潘公文集序》,第24册,第3666页
[27](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十一《戊申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92页。
[28](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十一《戊申封事》,第592页。
[29](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十一《戊申封事》,第592页。
[30](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答吴尉》,第3118页。
[31](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答吴尉》,第3118页。
[32](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O三,第2608页。
[33](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答范伯崇》,第1784页。
[34](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金华潘公文集序》,第24册,第3666页。
[35](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三《答胡季随》,《朱子全书》第22册,第2527页。
[36](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三,中华书局1986年,第227页。
[37](汉)徐干:《中论》卷上,《钦定四库全书》,叶11 A 。
[38](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七,第23册,2714页。
[39](宋)程顥、程颐:《河南程氏粹言》卷一,《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90页。
[40](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三,中华书局1986年,第229页。
[41](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三,第222页。
[42](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三,第244页。
[43](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三,第222页。
[44](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24页。
[45](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三《读余隐之尊孟辨》,第24册,第3547页。
[46](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三《读余隐之尊孟辨》,第24册,第3547页。
[47](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三《读余隐之尊孟辨》,第24册,第3547页。
[48](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二,第24册,第3884页。
[49](宋)朱鉴:《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说》卷八,《元明刻本朱子著作集成》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页A面。
[50](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十一《戊申封事》,第20册,第602页。
[51](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十二《己酉拟上封事》,第20册,第6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