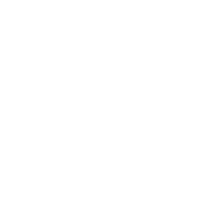云 谷 山
朱谷山
写下这座山的名字时,我倒没有责怪自己对它寻访得太迟,但在内心里,似乎却迟迟没有原谅自己对它的无知。
这座山叫“云谷山”,位于闽北建阳莒口镇东山村境内,原名“庐峰”。八百多年前,理学先贤朱熹来此结庐读书,游遍了这座海拔高达999.3米,与武夷山交界的主峰,以及蜡烛山、冲水岩、四角塔、蛇仔岗、莲花岗等五条山脉。朱熹足迹所至,发觉这里古木苍翠,花草葳蕤,涧水飞流,奇石侧立,宛若人间仙景。待攀上山顶,四下眺望,他不禁连连赞叹道:“庐山之巅,处地最高,而群峰上蟠,中阜下踞,内宽外密,自为一区。”更让他为之惊叹的是他数次重游后发现,此山“虽当晴昼,白云坌入,则咫尺不可辨;眩忽变化,则有廓然莫知其所如往。”因此他老人家大约是激情澎湃难抑,或是听弦知歌,心中豁然,便大有深蕴其意地把“庐峰”更名曰“云谷”。从此,云谷山这个名字,就在当地百姓嘴里口口相传下来了。
纵观朱熹一生,似乎是个理性高于一切的人,但从他对云谷山赋予的人文亲和力和诗性的钩沉方面看,他其实又是一个相信万物有灵、敬畏天地所有的生命的人。这里,虽是他的一个暂居之地,他却视之为精神故乡。由此,他完全被这里的山水所吸引,并以他的本真的体验,为这里的山水打下了他的文化印记。例如,他酷爱这里的白云,便把“庐峰”改为“云谷”;他留恋这里的山水,便深情地表示要在这里“耕山、钓水、养性、读书、弹琴、鼓缶以咏先王之风”,并说此举“亦足以乐而忘死矣”!这在朱熹一生的言行里,实属罕见。
1175年,朱熹在云谷山中修建晦庵(又名“云谷庵”)著书立说,还把主峰“一顶”命名为“赫曦台山”。就在这一期间,他不但亲自为云谷山撰写了特有灵气的美文《云谷记》,还亲自命名了山中二十六处景点,每处题诗一首,称之“云谷二十六咏”。
朱熹,就是这样自觉又自然地融进这个地理空间。
八百多年后霜降时节的一个早晨,我来寻访云谷山。从铺满梯田的山脚望上去,山色依然透出一派浓绿。细看,那绿中竟有好几种颜色:葱绿、翠绿、幽绿、浅绿。隐隐的,那绿中都似有晨光的莹亮,一闪一闪地投下斑驳的流影。再一细看,那一弯山垅上还散落着几棵柿子树,有不少柿子像红灯笼似的挂在枝丫上,与溪涧旁几丛鹅黄的野菊相映成趣。我不禁想到,若从那边的溪涧上山,是否会看到朱熹笔下的《南涧》:“危石下峥嵘,高林上苍翠。中有横飞泉,崩奔杂奇丽。”但东山村的向导老李立即否定了我的想法:“那条路走不得!当年朱熹才41岁,传说他健步如飞,但却惊叹峰回径转,我们还是沿着有一些石磊台阶又顺着山势而上的旧路上去。”
细问得知,原来由于年代久远,人迹罕至,那条被人称作“危石飞泉”的南涧已接近湮没,无路可走了。正说着,老李突然叫了起来:“看,云来了!这是朱熹最喜欢的景致!”
我抬头望去,只见空中如变戏法似的飘来万千缕白云,轻纱般地徐徐汇聚到半山腰,有的还未落定,飘飘袅袅地涌动;有的低回留恋,轻轻盈盈地腾挪;一团团,一片片,忽而散开,忽而融合,散发着一种蓬松而轻柔的乳白色。慢慢地,所有的云片云丝都互相融在一起,编织出一条巨大的白色腰带,紧紧绾住了云谷山。过一会儿,那腰带又缓缓流动着,叠叠相承又变幻不定地朝山谷飘去。
云谷山的云,真是把人看呆了。
上山时,我和老李都有些兴奋,不停地说这说那。因为,我们方才看到的云景,都还在各自的心中翻腾不已。不过,走了好长一段路,也没踩到几块旧时由农夫和樵夫们铺砌的垒石,倒是愈觉山深树老、曲折回亘。此时,轻柔的光线,淡蓝的薄雾,还有隐约中听到的哗哗溪声与阵阵鸟鸣,似乎预示着前方会有一个生气勃勃的世界。
然而,好不容易到达朱熹当年著书立说的晦庵时,左看右看,我只收获了一份不无失落的怅惘。原来,朱熹在《云谷记》中描述的庵堂四周,如今只剩得一块呈阶梯状的石头砌成的地基。三间草堂,不复再见;堂前原有“隙地数丈”,“植以椿桂兰蕙,茂树修竹,翠密环拥”,也早无影踪;倒是四周生了谢、谢了生的杂树,一直顽强地生存下来,成了这一沧桑的历史见证者。我走上前去,手抚着这些杂树,这才慢慢感觉它们确实没有颓唐的样子,反而有一种别样的亲切和诗意。不是吗?时间的流转,从古至今的世界已经不同了,但这些杂树还以它们的方式不断演绎着春秋冬夏,即便在冬天来临的时刻,它们的枝条还是簇新的。
在这里,我听到了一段所有人听后都会马上记下的故事:当年,朱熹在此建起草堂后,他的得意弟子蔡元定追随来到东山村,并在云谷山对面的西山上结庐苦读。虽说两山对峙,但还是有一段距离,要想互相喊话是听不见的。但在晴天的夜晚,两处都点起灯光,却微微可见。师生两人因此相约:学遇困惑时,夜间则“揭灯为号”。次日,相互往来,共探疑难。
听了这则故事,我不禁沉默了许久,惹得站在身边的老李忍不住问我:“您没事吧?”我说:“没事。”
其实,我注视着那段残存的石板地基,心里在感叹时间的无情、风雨的锈蚀……但我却分明从砖瓦之中,仿佛看到了一簇不息的精神之火,还在幽幽微微燃烧着。我相信,这一簇火焰,既留存至今,当会代代相传下去。
据说,朱熹在云谷山时,只想一心读书写作,常常谢绝朋友来访。他这样做的另一原因也是考虑到,当时云谷山交通不便,要来这里,须“缘崖壁,援萝葛,崎岖数里,非雅意林泉,不惮辛苦,则亦不能至也”。有趣的是,他竟在云谷山小山之东,筑一山台景点,题为《挥手》。他在诗中这样写道:“山台一挥手,从此断将迎。不见尘中事,唯闻打麦声。”因没有人来打扰他,便少了迎来送往的事情,从此他可安心做他的学问去了。但这个“径绕山腹,穿竹树南出而西,下视山前村墟井落,隐隐犹可指数”的地方,在哪呢?我们离开晦庵后一路寻了许久,身上都出了一层微汗,也只寻了一个大概的地点,由于时间有限,来前急速阅知的有关云谷山中原有或被朱熹发现的景点,如“两崖苍峭石,护此碧泓寒”的石池,“山高泽气通,石窦飞灵液”的井泉,“亭亭玉芙蓉,回立映澄碧”的莲沼,还有“小丘横翠几,层嶂复嵯峨”的云庄,“涧里春泉响,种桃泉上头”的排蹊等等,都无法逐一细揽,只能走马看花,或远远投以一瞥,最后才一鼓作气,气喘吁吁地登上山顶。
擦擦汗,喝喝水,定神一看,果然是个浑然天成的壮美景观。老李挥手叫我朝北看去,但见眼底下浮现着的座座秀丽的山峦,竟是武夷诸峰。视线移动时,随即,一览无余铺开的,是一幅幅行气如虹又飞红簇翠的山水巨画。但见那苍茫连绵的远山,色彩变幻的云海,金包银饰的梯田,错落棋布的村庄,以及那飞流直下的溪河,纵横有序的路径,还有那一片片的软红稚绿,那一处处的灼灼青青,全都萦绕交织在一起,让人尽览了一种层次高华、彩晕烘托的奇幻仙景。
山顶上,有石屋三间,近乎百平方米,看似可居。老李介绍说,这石屋冬暖夏凉,而且近旁有泉水,可引以漱濯。但这石屋到底是谁建造的呢?老李说,很早以前,村里有老人说,这些石屋是清朝时一户猎人因躲避山中洪水搬到山顶修建暂居的。
最令我惊异的是,就在距山顶下方二三十米的一块坡地上,有一道观,道观门前,竟然并排屹立着两株据说也有数百年树龄的红豆杉。无疑,这是朱熹1179年离开云谷山到江西星子县任知君后才长出的珍稀植物。否则,它怎么也不会被朱熹忽略。
于是顺着山岩下来,近前观看,两树均有二十余米高,胸围须三人牵手才能合抱。高大的树杆魁伟挺秀,繁茂的枝叶遮天蔽日。正逢秋尽冬来时节,一些尚挂枝头的红豆显得晶莹剔透,分外夺目。
我看见地上还留有几颗未被捡走的红豆,它们在沉默松软的泥土上安然无声地躺着。从没有奢望与红豆亲近的我,这一回再也忍不住,悄悄地捡起了其中的一颗,吹了吹尘土,便轻轻地揣入怀中。我想,明日回到家中后,我会端出一碗清水,轻轻地、认真地为它洗尘。或许,我还会和红豆说一句话:感谢你,自古朱熹走后,你已为云谷山守望了几百年。
下山时,老李经不起我一再撺掇,带我下到南涧走了一小段。这南涧,茂树交荫,巨石相倚,水流其间,声震山谷,连当地都没有几个人敢去探险。但我向来喜欢野性的水,认为不驯的水有不驯的美,有一种蓬勃和激烈的冲劲,叫人敬畏也叫人向往。果然穿过灌木丛下到溪涧一侧,但见溪中乱石如垒,两旁徒绝险峻,泉流自高泻下,诡匿侧出,淙散激射,刚烈与柔情迸进,叫人为之心惊也为之狂喜。为安全起见,我们互相牵手站立在一块巨石上仔细观赏,看见前面恰有一方不大的水潭,倒映着奇崖秀壑,自然错落,莹金耀银,如梦如幻。我发现,这云谷山的泉水,就是不同凡响,不管是涧中、沟底、滩前,那水是一色的清莹凝润,闪亮灵动;但流到不同的地方,水色或呈碧绿,或呈黛蓝,在不同的光线和山影树丛间,变幻着万千奇异的色泽。凡稍见平坦的地方,那水面是清澈如镜,倒映着坡谷、绿树、花枝,层次明晰,色彩斑斓。水边,大都花草丛生,藓苔蔓络,其景色秀美,令人眼花缭乱。飞泉溅处,用手捧一把水流,指缝泄落的,是一串银白色的珍珠。回想当年朱熹徘徊在如此夺人心魄的山水间,胸际间所涌起的,自然是一种不期而遇的温馨甘美和生机勃勃的诗情。
云谷山是生意盎然的,也是和谐宁静的。也许因为这里人迹罕至,使它脱却了人间喧嚣的气味,保持了一份万物绽放光彩、大千朝气蓬勃的态势。不过,至今想来,云谷山最有幸的是被朱熹赋予了文化意识。
转回下山路上,掠过茂密的树林,急湍的泉流,那散落于轻云淡雾中看似杂乱的草、细碎的花,以及一些蜂巢鸟穴,仿佛也得之天助,殊多意趣;更不用说随时可见的飞鸟、窜跳的野兔和爬行的蚁群。我想,这里的自然生态,肯定会使来这里的“高人”少了优越的神情,凡人多了性情的流露。
老李突然记起什么,说:“前两年,村里的人还发现山上有东北虎!”
我有些愕然:“是华南虎吧?东北虎不可能跑到南方来。”
老李说:“反正发现过老虎,但还没有拍到。”随之他又说:“由于上面对云谷山进行保护和管理后,这里野猪变多了,山鸡、白鹇到处都有。”
我一听不禁笑了起来,点头对老林说:“这一切,首先应当感谢朱老夫子,正是他老人家当年在云谷山修建晦庵,还写下了《云谷记》和《云谷二十六咏》,免费为你们做广告,这云谷山才开始扬名了。”
老李一听也笑了,点点头说:“是啊,现在这里还留有朱熹手迹,如‘南涧’‘战龙松’‘赫曦台’等摩崖石刻。还有南宋理宗皇帝御书‘庐峰’,刻于安嶂山麓涧旁一座高约四米的圆锥形岩石上,每字一半见方,上款‘已卯赐蔡杭’,下款‘宝祐丙辰十月朔,太中大夫参知政事臣蔡抗刻石’。石刻字体苍劲,刻工精细,为闽北古代石刻艺术之精品。1992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听老李介绍,我心中不由得有些惭愧起来。不是吗?都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云谷山虽然没有神仙来过,但却迎来了朱熹,他写下的云谷山诗文,使一处鲜为人知的胜境,其知名度几与武夷山齐名。据说研究朱子学的海内外学者,几乎都知道建阳有座云谷山。但平日也学写诗作文的我,竟迟至今日,才得幸初睹云谷山,才在岁月的肌理深处,如饥似渴地读到了朱熹那刚健率真又不失野逸空灵的《云谷记》,以及落笔畅快又隐现清雅俊逸、鲜活透亮的《云谷二十六咏》。
下到山脚了,那枚远古的夕阳已挂在西山顶上,沉沉的云彩镶嵌着缕缕黄金,有点刺眼的光芒一下照射到我的那一颗因被山水触动而坦露的内心,我觉得周身一下变得敞亮和舒畅了起来。回望重峦奇嶂的云谷山,我突发奇想:要是朱熹还在山中,今晚,我定要携一壶老酒前去拜谒,听他讲云谷山的一切,听他以深厚的理学穿透漠漠乾坤,直到北斗斜时……
(本文原载于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省作协“走进八闽”文化采风系列之《走进建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