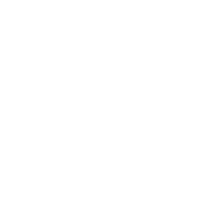美丽的月亮湾
马星辉
一
这是一个藏在深闺人未识的、流淌着诗情画意的、极具旅游价值的处女地。这里保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德与精彩,亦有着现代的时尚意识与浪漫。它便是延平区大横镇的月亮湾。
从闽北大山里走出的建溪一路向前奔向闽江,奔向浩瀚的东海。流经这里时留恋这块芳香的土地,特意放慢了前行的脚步。溪水弯曲蜿蜒、依依不舍,画出了一条两千多米长的美丽弧线,造就出一个半轮明月的黄金河岸——延平月亮湾。多情的溪水还带来了一湾洁净的纤纤细沙,在阳光的照耀下如金子般闪闪发亮。每当夏天来临之际,躺在柔软舒适的沙滩上,仰望蓝天白云,沐浴热情阳光,感受轻柔的风,难以言状的愜意快乐。它可以与江西婺源同名的月亮湾相媲美,只不过这里的月亮湾显得更娇小玲珑些罢了。
坐落在月亮湾怀中的小仁洲村(即博爱村)依山傍水,环境清幽,溪在村旁,流淌不息。村庄树木茂盛,花草处处,房舍栋栋,错落有致,端的是一个山清水秀、恬静安详的世外桃源。村中人家生活质朴,布衣蔬食,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快乐在悠然自得的田园之中。
这次我有幸参加由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与福建省作家协会组成的“走进延平”采风团,所领任务为延平区月亮湾的休闲旅游与涂鸦文化。有博爱村、金太阳农庄、鱼米山庄三个采访点。
二
第一个采访点是地处月亮湾中的博爱村,前往的那天上午,乌云压顶、电闪雷鸣,天似乎被捅漏了,滂沱大雨倾泻如注。恶劣天气几乎浇灭了采访的热情和欲望。大横镇宣传委员吴峰与宣传干事颜斐冒着大雨准时无误地到达闽北饭店。这让我深受感动,无二话,下刀子也要出发。
一路上雨愈下愈猛烈,汽车雨刮器左右来回疯狂地快速猛刷,车窗也如一幕水帘流淌不止,影响视线,前方能见度极低。汽车只能低速前行。夏天的雨就是十分任性,有些不善解人意,常常是急风暴雨,让人感到它是一种发怒,一种宣泄,没有理智,没有顾忌。据说掌管夏雨的是条血气方刚、脾气火爆的小青龙,平日里它就看不惯人类在自然界的狂妄称大,自以为是。所以每年遇到它夏季值勤之时,总是要给点颜色让人类瞧瞧。
文静典雅的宣传干事颜斐小巧玲珑,看上去像刚走出校门的女大学生,不曾想她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六个年头了。看着车窗外的瓢泼大雨,她不无担忧地说今年的雨汛比往年提前了。1998年闽北遭遇百年不遇的“6·22”特大洪灾,小仁洲村损失极为惨重。从6月初开始雨就下个不停,水位几次超过了警戒线。到了6月22日那天,黑云密布,电闪雷鸣,瓢泼的雨水向人间铺天盖地倾盆而泻,才几个时辰的功夫,地上大水横流,漫山遍野。来势迅猛的特大洪水淹没了小仁洲,全村近200户人家的房屋被冲毁,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200多万元。待夏雨平息了下来,小仁洲己是满目疮痍、家园尽毁,百分之七十的村民无家可归。美丽的金沙滩成了一片黑乎乎、脏兮兮的烂泥潭。小仁洲村受此百年一遇的重创,要想恢复原气谈何容易。人们不禁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原本充满了快乐的月亮湾失去了往日的欢笑声。
所幸,灾后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村民奋起抗灾自救,重建家园。政府在小仁洲村尾205国道旁推开了一大片宅基地兴建新村,不到一年的时间,村民们住上了温暖的新居。在此期间,除却政府的拨款外,还得到福建省红十字会的鼎力支持,包括新华社香港分社转来香港和台湾红十字会捐赠人民币186万元。小仁洲村渡过了难关,恢复了正常。村民为感谢党和政府、感恩社会各界对小仁洲村灾后重建的支持,1999年改村名为博爱村。2006年成立了全国首个村级红十字会,期间,为云南普洱、汶川大地震、玉树大地震、台湾“8.8”风灾、雅安地震、鲁甸地震等重大灾害开展募捐,共募集善款13.5万元,通过上级红十字会转往灾区,表示同情与爱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怀有感恩之心是博爱村人质朴的传统美德。
三
汽车沿着205国道行驶约一小时,到达目的地博爱村。大雨逐渐转为小雨,田野四周弥漫在一层轻纱般的薄雾之中,不远处的月亮湾呈现出一种朦胧的景致韵味。走进村头,一座小巧玲珑的村级公园出现在眼前。公园倚山临溪,视野开阔,缓缓而流的月亮湾与对岸狮子山全景尽收眼底。村公园南面有一座明朝末年修建的龙兴宝殿,几棵百年大樟树郁郁苍苍、华亭如盖。紧挨着大樟树边立有一块大石碑,上面刻录文人雅士《瀛洲赋》一篇,其中写道:“金盘山美,狮子潭幽。闽江上游,金斗屏寺……”
颜斐介绍说,龙兴宝殿有一个传说故事,元朝年间有一次发大水,建阳倪坑祖庙的“二圣公”菩萨被大水冲到小仁洲村的樟树旁,村民们见了又惊又喜,认为这是“二圣公”菩萨看上了小仁洲这块风水宝地。为此村民们出资建起一座三进厅的龙兴宝殿,将“二圣公”供奉于正厅朝拜,终日香火不断。
说也奇怪,这年村里所有出生的孩子均为男丁,村民们不禁喜出望外,高兴逾常,说这是“二圣公”菩萨洪福所至。因为“二圣公”菩萨是农历正月二十二得道成仙的,所以村民们便定在这天搞庆典活动。凡所有生孩子的人家都杀鸡宰羊,做寿桃包、寿面塔。这天一大早大家争着给“二圣公”菩萨上头炷香,家主报上添丁的生辰八字,点上大红蜡烛,燃放鞭炮,庙门口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上写着“添丁发甲”四个大字。到了晚上大摆酒席吃“添丁酒”,包括路人和乞丐遇上了便是有缘,都视为座上宾,同喜同贺。全村人是喝了东家喝西家,家家户户地喝过去,直到一醉方休。这个“添丁节”民俗活动流传了几百年。不过现今“添丁酒”传统习俗简化了,只在正月二十二日晚上,添丁人家摆席宴请亲朋好友。
博爱村是个历史悠久的古村庄,有不少明清建筑,但在“6·22”特大洪灾中受损严重,至今旧村断垣残壁四处,着实令人扼腕。只有那历经岁月的古老青石,在雨水的滋润下散发出沧桑之光。据村里老辈人讲,村所在地是“龟蛇相会”的龙脉宝地。“蛇地”就是村头的龙兴宝殿;“龟地”则是村中的叶氏祠堂。早在明朝年间,“龟地”是一位身家富裕的叶姓员外住宅。这是一座少见的“七房厅”建筑,首进为正厅(即大堂迎客厅)、二厅为待客厅、三厅是议事厅、四厅为客人休闲厅、五厅为祖宗灵位厅、六厅是家人麻将厅,七厅为小姐娱乐厅。这座建筑内还有一条秘密地道,为遇到土匪及遭遇不测时所用。至今还遗留着地道口。大门前有花圃,有小池天井台、金鱼塘,塘边用青石板铺设,在“七房厅”大门口外左侧处也就是花圃左侧有口水井,井水可以饮用,主要是用来防火的,现今这口井的所在地称为水井头,这条小巷村民则称之为水井巷。
四
听吴锋、颜斐介绍情况,边走边谈,漫步来到村中。博爱村是个大自然村,住有五百多户人家、2000多人口。但此时人却不知道上哪里去了,村庄显得十分恬静安然,只有淅淅沥沥的小雨声在耳边沙沙作响。吴锋说,村里的年轻人都往城里打拼去了,这两年有条件的又把家里人也带走了,所以村庄显得人气不旺。是啊,在城市化的浪潮中,不计其数的村庄包括传统的古村落毫无招架之力。大批农民进城务工,人员与劳动力向城镇大量转移,致使村落的生产生活瓦解,空巢化严重,已经出现了人去村空。从“空巢”到“弃巢”的现象日益加剧,这正是眼下农村的普遍状况。但这种状况是社会发展变革时期的必然现象与规律,任何人都无良策拦阻与改变。然而,我相信总有一天,逃离乡村的人们会回归故里,不再远离。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他们来说,无论走到哪里,在外面是发达还是落魄,是事业有成,还是一事无成,皆是无根的漂泊,谁都难忘故土,难忘家乡。因为故土有太多、太多令人魂牵梦萦的乡愁……
雨幕中有几只春燕从眼前忽然剪飞而过,目光不由自主地追随鸟儿而远。兀地,只见连片的荷花池映入我的眼帘,但见莲荷亭亭玉立、绿萍斑斑点点,呈现一片清新悦意之景。如北宋词人欧阳修所云:“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景色美不胜收,我等不禁驻足留连,细细观赏起荷花来。
博爱村的荷花与别处不同,它特别养眼耐看。别处的荷花大都在池中长得太多太足,显得密集而拥挤,让人难以细品细赏。而这里的荷花分布得恰到好处,不密亦不稀,不多也不少,株距恰好。荷花更是长得纤纤精致,清秀小巧,均如同新荷一般保持着苗条的身材。池中浮萍分布得也均匀,比例得当,萍不与荷争芳,荷不与萍相离。整个画面就如经过画家精心布局的一幅风景画,呈现出唐代诗人李群玉的《新荷》所绘“田田八九叶,散点绿池初”的那种美妙。
待走近荷田跟前时,我惊喜地发现竟有两只野鸭在荷下悠游,见到有人来也不惊恐失措,而是神情安然依旧,一副旁若无人的模样,煞是可爱。由此可见博爱村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程度。
博爱村分为新旧两个村庄,新村新楼现代时尚,温馨舒适;旧村旧居断垣残壁,荒凉芜秽。这是当年“6·22”特大洪灾所致。正因为如此,为博爱村的“涂鸦文化”提供了难得的场地与氛围。最早是闽江学院美术系的大学生们在此实习写生,大概是不忍看旧村的孤寂冷落与死气沉沉,走时留下了一些涂鸦画作,以增加一些人气。不曾想为后续而来写生的学生们开了个头,愈发热闹起来。学生们先是在旧村的断垣残壁上涂鸦,后来发展到在有人居住的新村家居墙上作画。涂鸦画作几乎布满了整个村庄,内容也十分丰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作品,也有西方风格的新潮画作:二十四孝图、增广贤文、燃烧的太阳,明亮的星星,调皮的猴子、可爱的海豚等,栩栩如生、风格各异。他们画风景,画动物,还有抽象符号、卡通漫画等,为传统的古老村庄增添了浓浓的现代气息。
“涂鸦”原本是贬义词,出自唐朝诗人卢仝《示添丁》一诗中:“忽来案上翻墨汁,涂抹诗书如老鸦。”说的是其儿子乱写乱画顽皮之行。后来中国文人则以“涂鸦”比喻书画或文字的稚劣,以示自谦。时至现代,各种随手涂抹在建筑或物品上的文字、图画、符号等,都被认为是涂鸦。大多数的人将它视为一种污损、疯狂、侵犯、恐吓。但也有一些人认为涂鸦是一种美学性产物,是被压制者或没有发言权者的个性独白。
这让我有些出乎意料之外,哪怕是福州这样开放、包容的都市,虽然允许涂鸦文化存在,但主要集中在人居较少的高架桥、隧道附近,如象山隧道、屏东红墙巷、三县洲大桥、闽江堤岸等地方。不少人对涂鸦并不支持,甚至还有一些人明确表示反对。故而,在一个传统观念十分浓厚的小山村竟然流行时尚的涂鸦行为,这让人感到有些稀奇。我问小颜,这里的村民允许在自己的门口大墙上涂鸦么?难道他们一点也不反对么?小颜不假思索地说,不会啊!不仅不反对,而且是十分乐意。你看,眼前这幅“愤怒的小鸟”就是这家老奶奶请学生们特意为她小孙女画的。
看来确是如此,从博爱村的村名,从村头的村级公园,从全国都少有的村级红十字会,包括老奶奶要求大学生为她孙女涂鸦“愤怒的小鸟”的新潮,博爱村这个古老的山村己经敞开了接纳现代世界的胸怀。
五
月亮湾是大自然赐给延平的珍贵礼物,它的确是一个赋有特色,可遇不可求的旅游景地。但实事求是地说,目前它还是处在初级阶段,与延平区其他历史悠久的王牌旅游景点相比,不过是刚刚起步而已。这或许是延平旅游资源密集程度高的缘故,一时无暇顾及月亮湾的旅游开发。延平倚千峰竞秀的茫荡山,临风光俏丽的延平湖,多姿的九峰山、玉屏山,点缀其中,相得益彰。形成了山、水、城融为一体的独特景观。城郊近处有溪源峡谷、石佛山、古道三千八百坎、莲花山、天湖、宝珠、高坪鸳鸯石等众多的景点。尤其是名声远播的茫荡山,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素有“福建庐山”之美誉。景区内物种众多,高等植物有2000余种,树种是欧洲的三倍,国家重点保护和国际性协议保护的动植物达200多种。故而,对小巧玲珑的月亮湾一时未能顾及,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近几年随着京台高速公路、南平高速公路联络线的建成通车,延平区大力推进乡村休闲旅游发展。提出“福州后花园”这一定位,加快建设一批山庄、果庄、鱼庄等。这其中包括月亮湾的旅游开发。打造以博爱村为主,附带金太阳农庄、鱼米山庄,形成美丽乡村、传统村落、农家休闲的旅游区域,突出古廊桥、古井、古庙宇、古建筑、古民俗、古梯田等古元素,开发避暑养生、休闲娱乐、修学度假、涂鸦写生、水上游乐等旅游新项目。
金太阳农庄距博爱村2000多米,占地80余亩,有连栋育苗大棚2万平方米,计划投资1000万元,目前已完成投资550万元。以花卉观赏、生产种植为载体,是一个集餐饮、花卉种植、果蔬采摘、农耕体验、休闲观光为一体的休闲旅游农庄。农庄有牛奶草莓种植采摘区15亩,约10万株的葡萄(夏黑)采摘区5亩,古田优质水蜜桃采摘区25亩,年产东方百合20万枝,销往上海、广州、厦门等地。去年10月对外开放花海观光旅游项目,截至今年3月累计接待游客约1.5万人次。农庄年产值约500万元,利润150万元,农庄现有固定员工12人,农艺园艺师3人,专科学历管理人员2人,每年雇佣当地农村闲散劳动力(零工)累计近千人次。农庄在今年计划完成1500平方米综合用楼建设,以及300米的沿河栈道,提高游客休憩、观景的质量水平。
鱼米山庄与金太阳农庄相隔不过600米,以提供水产品与垂钓为主。辟有80亩水面,主要品种有鲫鱼、草鱼等,渔村一次性可接待200余人餐饮,亦有适合年轻人的自助烧烤项目。同时附带销售活鱼、土鸡、土鸭、蛋,竹笋、香菇、柑橘等农产品。大横镇宣传委员吴峰信心满满地说,大横镇的规划是把博爱村的写生基地、涂鸦文化与金太阳农庄的花卉市场、鱼米山庄的农家生活连为一体,互通有无,相得益彰,形成一个佳美、舒适、内容丰富的月亮湾休闲旅游胜地。
傍晚,雨停了。月亮湾沙滩上传来了挖掘机的轰鸣声,村党支书叶德明告诉我,这是博爱村今年投入45万元在清理2公里受污染的沙滩,届时月亮湾沙滩将恢复美丽的原貌。我看到了月亮湾的美好明天,听到了月亮湾的笑声。
六
回到城区,己是华灯初上时分。高楼大厦霓虹闪烁,明翠阁、延寿楼、双溪楼、望江楼四大阁楼灯光灿烂;九峰山麓亭台水榭,玉屏阁流光溢彩,绿荫丛中透出层次分明的光芒。延平城真不愧“小重庆”之别称。我想,此时月亮湾的沙滩上也是灯火通明,挖掘机的轰鸣声在唤醒沉静了许久的土地,博爱村涂鸦墙上的“愤怒的小鸟”与海豚、猴子、小熊这些动物精灵们,说不定溜下墙壁与孩子们在夜幕中尽情联欢……
其实,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类似月亮湾这样美丽的天然景点不胜枚举,只是这些年过度的经济开发,破坏和毁灭了不少原本环境优美的资源。在采访中我看到,月亮湾周边的阔叶林被砍伐得太厉害了,那些几乎被砍伐殆尽的阔叶树,在短短的几年,甚至几十年内是无法修复的。否则,月亮湾的山会更青,水会更绿。
如果天空不再是蓝色的,小鸟不会飞翔;江河不再清澈,鱼儿就会离开家乡;空气不再清新,花儿就会失去芬芳。先辈们无法对留给后人的资源明确产权界定。按照“物质不灭”定律,今天我们赖以生存、喜爱、享受的任何基础和条件,均是以消耗一定的资源成本为代价的。而被消耗的许多资源、如煤、油等又是不可再生的;即使那些可再处理或再生资源,如水、树木等恢复原生态的过程,又需要充足的时间成本和技术成本。很明显,假如用“边界原则”划分每代人应该享有的“资源主权”,财富增长将会有所节制,权力运用将能更为合理,历史将会变得更为有序。
(本文原载于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省作协“走进八闽”文化采风系列之《走进延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