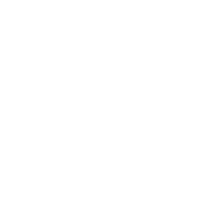·纪念沈葆桢诞辰200周年·
沈葆桢据理力挺船政大计
林樱尧
1807年8月,美国工程师富尔顿以蒸汽机为动力,在英国伦敦造出时速5英里的“克勒蒙特”号机动船,标志着世界造船工业的开端。约60年后,中国的清王朝在福州马尾、上海高昌庙,分别创立了福建船政和江南机器制造局,我国机器造船也由此发轫。新生的中国造船工业起步维艰,但仍顽强地向前迈进。因为,建设海军抵御外侮,是当时洋务远动倡导者和实践者的思想动力。
19世纪70年代初,马尾、江南两厂已造出兵商轮船近十艘,发展势头看好。正当两厂致力于扩大造船生产规模之际,却有几位颇有来头且地位不低的权贵跳出来,无视新兴的中国造船工业于国家海防有着重大意义并已取得成就,公开发难,阻挠造船,其中代表人物便是内阁学士宋晋。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造船“应否裁撤”的大争论。
这场风波源于一份来自船政的奏折。1870年10月26日,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的父亲沈廷枫逝世,奏准朝廷居家守制。奉旨,船政事务暂由提调夏献纶、吴大廷办理,而需奏咨事项则“禀知将军、督、抚等代奏”。这一时期,船政已造成4艘轮船,第五艘业已下水,且第六、七、八号船舶也已相继开工。轮船建成了,但养船费用日增,经费开支短绌。按左宗棠当年规划,“成一船即练一船之兵,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可以布置沿海各省,遥卫津、沽”,但他尚未考虑成船后所产生的费用问题。对于这项养船经费,沈葆桢刚上任之始则已预见到了,他在同治六年(1867年)六月十七日正式接事之日奏上《船政人事日期折》中就提到,“至于成船之后,一船又有一船之经费,非放开眼界,通盘筹划,虽竭帑藏,不足以供之”。当时朝廷接奏后,对这一问题先是肯定了沈葆桢的见识,褒其”清慎之怀,中外共见”,解决方案则是到时请福建地方官员“务当和衷商办”。转眼几年过去,养船经费凸显,船政提出两个解决方案:一是以福州、厦门海关“洋药(即鸦片)税款,用于“养船”;一是将成船分派各省海口,由各省承担部分费用。两个方案也曾试行实施,但因福州、厦门海关近年“洋药”进口量递减,税收减少,多有不足,而调拨各海口之船,如“湄云”号先拨浙江效力,因与当地水师关系没理顺,又退回船政,“万年清”号拟拨天津,因该船吃水过深,与当地海口“不甚相宜”,未能接收,此事就拖了下来。
沈葆桢开始丁忧守制当天,署理闽浙总督文煜会商沈葆桢后,在奏陈各号轮船制造情形折中,附片奏称:“再,闽省新造轮船,配拨弃、兵、舵、水人(水手)等应需薪粮、公费及煤炭经费,前经奏明,将福州、厦门两口洋药票税一款,截留专用在案。兹查洋药票税每年征银不过八万两,近来洋药滞销,票税尤形短绌。而轮船大号者每月薪费约支银二千一百余两,小号者每月薪费约支银一千五百余两。现成大号船三只,小号轮船两只,每月需银九千余两,又建威夹板练船,每月除洋员薪水外,需银一千一百余两,已不敷支给。”文煜附片中罗列了各种养船开支已大大超出原定的福、厦两口海关洋药税收,船政经费已难以应付,进而还指出“以后成船日多,经费动支更钜”,希望有个稳妥的解决办法,“不能不通盘筹及”。文煜所提的问题,亦是沈葆桢所思虑的,所以片中再次提出“伏查创造轮船,原为中国自强之计,沿海各省必须协办通筹,分拨应用,在各处洋面,既资巡缉,而往来港道,亦易熟谙。”请求朝廷能让船政成船由各省海口认领,以减轻船政负担。
文煜附片奏上之后,朝廷批给总理衙门,让“该衙门议奏”。总署奉旨,经与分管财政的户部往返商议,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让浙江、广东、山东、奉天、天津各口认领船政所造之船,江苏一省则认领江南制造局所造的兵船。养船费用准许 “各该省洋药厘金项下,就近动支,仍核实支销,毋许浮滥”。同治十年(1877年)十一月初六日,总署将方案方上报皇帝,次日奉旨:“依议”。也就是说,在总理衙门协调下,船政养船费用支绌的难题,有了初步的解决方案。
正当总理衙门奉旨协调落实船政轮船分拨各省调用之际,内阁学士宋晋突然发难,于同治十年十二月十四日上疏朝廷,奏请停造轮船。其奏文一开始就下了定论:“闽省连年制造轮船,闻经费已拨用至四五百万,未免糜费太重。”其理由有三:一是朝廷已有议和之策,不必再有武力制夷之举,并认为这是“猜嫌之举”;二是自己造的船“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便,名为远谋,实同虚耗”;三是若“用以巡捕洋盗,则外洋本设有水师船只”,“何必于师船之外,更造轮船,转增一番耗费”;四是“将专用以运粮,而核其水脚数目,更比沙船倍费。”所以,他主张“应请旨饬下闽,浙、两江督臣,将两处轮船局暂行停办”,对已经成造的船只,拿去出租。
宋晋(1802—1874),字锡蕃,号雪帆,江苏溧阳人,道光二十四年进士,清流派代表人物之一,喜欢说三道四。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时,他竭力维护清朝统治,屡屡上书指责各地剿战不力,曾以一年中上疏数十章而扬名。他一生任京官,在镇压太平军战争中,曾先后推崇曾国藩,举荐左宗棠、沈葆桢,名声不小,其言论颇受时人重视。1866年6月,闽浙总督左宗棠上疏在福州马尾办船政,指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制造轮船不可”的真知灼见,得到了朝廷的充分肯定。上谕还特别强调:“中国之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该督现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当之急务……左宗棠务当拣派要员认真讲求,必尽悉洋人制造、驾驶之法,方不致虚糜帑项。所陈各条,均著照议办理”。
如此一项国家级大工程,作为一个深谙官场游戏规则的封建士大夫,宋晋断不至于无端突发奇论。他敢公然反对新兴的造船工业,而当时倡导造船的都是地位显赫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以及皇室贵族恭亲王奕訢等洋务派,自是摸准了最高统治者的脉膊,也迎合一批保守派的心态。昏庸的保守派根本就看不懂闪烁着现代科技光芒的新生事物,对“师夷长技”十分反感,虽然鸦片战争后屡遭列强欺侮却不醒悟,依然偏执于昔日北方部落的“铁骑辉煌”,对于造船、建设新式海军等,都认为是“一片胡言”。基于如此背景,宋晋跳出来大肆反对船政,也就不足为奇了。
本来,一股落后的思潮,掀不起什么波澜。宋晋也不是什么得意的大人物,可出乎意料的是,清廷最高统治者却迅速批转宋晋奏折,谕令署闽浙总督文煜、两江总督曾国藩“通盘筹划,应否将轮船局暂行停止之处,酌量情形,奏明办理”。接旨后,文煜以模棱两可的态度答复朝廷。而曾国藩则委婉陈辞,认为“刻下只宜自咎成船之未精,似不能谓造船之失计;只宜因费多而筹省,似不可因费绌而中止”,坚持造船的态度还是明朗的。曾国蕃在奏议的最后,则更是坚定地表明:“趁此内地军务将竣之际,急谋备御侮,非好动也,仇不可忘,气不可懈,必常常有设备之实,而后一朝决裂,不至仓皇失措!”讵料,曾国藩奏上仅过5天,尚未得到朝廷回复,即于1872年3月12日因病辞世。清廷最高统治者似乎不遂心愿,又责成军机处发布上谕,命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就造船“应否裁撤”表态。一项事关中国新兴造船工业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严峻地摆在了左、李、沈诸人的面前。
左宗棠是福建船政的倡办人,此时他正在陕甘总督任上,虽置身西北边陲,仍心系船政和造船。1872年4月2日,他率先上疏,态度鲜明,力陈制造轮船“实以西洋各国持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技以制之。……窃维此举为沿海断不容已之举,此事实国家断不可少之事”。他驳斥那些无事生非者,“若如言者所云,即行停止,无论停止制造,彼族得据购雇之永利,国家旋失自强之远图,隳军实而长寇仇,殊为失算”。左宗棠还明确表态,若船政经费确实困难,可以把闽省应拨付西北的军费留给船政使用,全力支持船政继续造船。
李鸿章是江南制造局的开创者之一,当年曾国藩委托容闳从美国购回100余台机器设备,悉数拨归制造局使用,本意是制造枪炮,但也先行造船。不知出于什么心态,理应以维护造船大局为己任的李鸿章,在这紧要关头,却态度暖昧。他在1872年2月29日复福建巡抚王凯泰的信中也认为:“闽船创自左公,沪船创议曾相,鄙人早知不足御侮,徒添糜费”。随后,在3月5日复曾国藩的信中,他态度有所转变,说兴造轮船虽为自强一策,但因造船花费大,一时尚不能御侮,易遭人口舌。表露了他的苦衷和疑虑。
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则旗帜鲜明。早在船政开办之初,本当鼎力相助的闽浙总督吴棠却囿于成见,胡诌什么“船政未必成,虽成亦何益”,并藉端打击船政提调等人,从中掣肘。沈葆桢十分恼火,专折上奏,据理力争。清廷不得不将吴棠调任四川总督,为福建船政的最初发展搬走了一块绊脚石。在沈葆桢掌管福建船政的几年中,虽不时有人冷言冷语,讽刺打击,无端干扰,沈葆桢均不为所动。他十分理解当年左宗棠所列的设厂造船“七大难”,其中“至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始则忧其无成,继则议其多费,或更讥其失体,皆意中必有之事”。看准了只要于国计民生有益之举,定当奋力向前。现在又有这么一股势力公开阻挠造船,且举理之歪,令沈葆桢深感气愤。
同年5月7日,他继左宗棠后立即上疏,言词激昂:“查宋晋原奏称‘此项轮船将谓以之制夷,则早经议和,不必为此猜疑之举’。果如所言,则道光年间已议和矣,此数十年来列圣所宵旰焦劳者何事?天下臣民所痛心疾首不忍言者何事?夫恣其要挟,为抱薪救火之计者,非也;激于义愤,为孤注一掷之计者,亦非也。所恃者,未雨绸缪,有莫敢侮予之一日耳。”他接着痛驳宋晋的滥调:“原奏称‘用之外洋交锋,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便,名为远谋,实同虚耗。’夫以数年草创伊始之船,比诸百数十年孜孜汲汲、精益求精之船,是诚不待较量可悬揣而断其不逮。旋亦思彼之擅是利者,果安坐而得之耶,抑亦苦心孤旨不胜糜费而得之耶?”,“外人之垂涎船厂非一日矣,我朝弃则彼夕取。……今无故而废之,一则谓中国办事毫无把握,益启其轻视之心;一则谓中国帑项不支,益张其要求之焰“。而后,他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此微臣所以反复思之,窃以为不特不能即时裁撤,即五年后亦无可停,所当与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永垂不朽者也。”
沈葆桢疾言维护造船大计,决非出于对宋晋的私人成见,更不是担心自己的船政仕途半途而废。他在马尾工作数年,大量接触了西方经济思想和科学技术,看到先进生产力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他认为,建造舰船、建设海军,增强抵御外来侵略之国防实力,是重要的一面。若“停造”、“裁撤”势必“尽撤藩蓠”。不但于此,“外人垂涎船厂非一日矣,我朝弃则彼夕取,始也以借用为言,无辞以却之也”。如果这样,不但中国的海防建设无从谈起,船舶修造以及航运,又将操于外人之手。若按宋晋之言行事,正中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害怕中国强大的下怀。沈葆桢的新潮思想还不仅局限于此,他还以发展的眼光看到,中国还应当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造船的基础上,奠立起自己的民族工业基础。沈葆桢从不同方面剖析造船的得失、成败,坚决不同意停止造船。
有远见就有胆识。在5月7日的上疏中,沈葆桢不但反对“停造”,相反,而且提出进一步发展的设想。他主张,首先还得筹费,一是“海关五万,按月解给,且恐万万不敷”,最好再增加。若一定要减省,则要等五年限满后,将外聘洋人遣散才能谈起。但他又提出,辞退洋员省下的经费,还不能上交,应当用于人才培育,他奏道:“御侮有道,循已成之法而益精之耳。洋人来中国教习,未必非上上之技。去年,曾国藩有募幼童赴美国学艺之举,闽工欲踵而行之,以艰于筹费而止。拟限满后,选通晓制造、驾驶之艺童,辅以年少技优之工匠,移洋人薪水为经费,以中国已成之技,求外国益精之学,较诸平地为山者又事半功倍矣。”二是要增加成船后的海军训练,“否则士卒不习,虽极精之船,亦块然一物耳”。此时,沈葆桢已在筹划建立海军舰队,“前蒙特简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为轮船统领,俾常月训练,惟是训练不能无费,该提督索性廉介,必不思藉润乎其中,而缺瘠家贫,力不足以赔垫。臣旋即丁忧交制,未及奏请,应恳饬下督抚臣,按月筹解五百金,为该提督出洋操费”。
针对藉端“糜费太重”而引发的停造之争,沈葆桢非但不避人家攻击的锋镝,还针尖对麦芒地要求“但兵船为御侮之资,不容因惜费而过少耳”。他痛声疾言之间,并未一味强调多花钱多投入,而是多方说明,能省的费用应当省,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
令人感慨的是,竭力倡导西方科技的沈葆桢,在极力驳斥停止造船谬论的同时,还不忘向上报告现代科学的重要性,尤其是数学这一学科,更要学习并普及。他奏曰:“西法虽千头万绪,要权舆于算学。中法与西法,派虽别而源则同。臣尝会同前督臣英桂,有请设算学科之奏,部臣因无人可以阅卷议驳。然闻京师同文馆教习李善兰,通西学者也,前任山西河东道杨宝臣,通中学者也,倘废无用之武科以励必需之算学,导之先路,十数年后,人才蒸蒸日上,无求于西人矣。”
以国家安全为己任,无私才能无畏。沈葆桢慷慨陈辞,自然也鼓起一大批有识之士之勇气,附和者众,李鸿章也收起动摇之心。在这之前,李鸿章曾遣派幕僚盛宣怀到马尾实地考察,意在通过亲信调研,摸透船政底细后再表态。盛宣怀奉命来到马尾,沈葆桢不知其意,但与他晤谈后,对其评价甚高。《马尾港图志》记载,沈葆祯曾对随员林贺峒说:“今日觏一奇士,其将为国家任事之人乎。与之谈郡国利病,烛照数计,老于吏治,不是过对。使函答,顷刻逾十纸。”盛宣怀赞成沈葆桢观点,认为船政继续造船利大于弊,回复了李鸿章。1872年6月,李鸿章上奏《复议轮船制造未可裁撤折》,批驳宋晋等人,并讽之“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之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扭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巨创而痛深。”李鸿章的表态颇有份量,最终扭转了停办船政之议。而李鸿章折中的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名句,发人深省,为时人争相传诵。8月2日,总署大臣奕訢也上奏,谈到“造船虽费多而艰难,成效一时也难显见”,“虽将来能否临敌制胜未敢预期,惟时际艰难,只有弃我之短,取彼之长,精益求精,以冀渐有进境,不可惑于浮言浅尝辄止”。继而他又婉转地陈述:“臣等于船厂未经亲历,实不知其详,惟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诸臣虑事周详,任事果毅,意见现已相同,持论各有定识,且皆身在局中,力任其难,自必确有把握,其间造船以资华商雇领一节,李鸿章、沈葆桢俱以为可行,应由该督抚随时查看情形,妥筹办理。”清廷见诸臣力陈利害,见解合情合理,遂作罢议。一场危及近代中国造船工业发展和海防大计的重大争论,就此平息。

百年老船政
在这场大争论中,沈葆桢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为新兴的中国造船工业争取到又一个发展空间。现在,史学界公认,我国近代工业,以造船为先导,并且以其独特的发展历程,成为中国工业的母行业。从这个意义上讲,沈葆桢为中国工业化社会的奠基和形成,立下不朽功勋,称之为“中国工业化之父”,亦足以当之。
(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