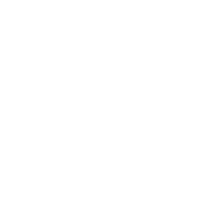寻找谷文昌的足迹
杨少衡
1981年1月29日,隆冬时节,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在东山。强劲海风在海面刮起大浪,东山岛林涛不绝,有一个消息传到省委书记那里:当年在此间率领干部群众植树造林、奠定满岛青翠的原县委书记谷文昌在百余公里外的漳州市区龙溪地区医院,病危。项书记连夜赶到漳州,准备去医院看望谷文昌,由于时间已晚,风雨交加,改为第二天去医院,却不料谷文昌于凌晨时分病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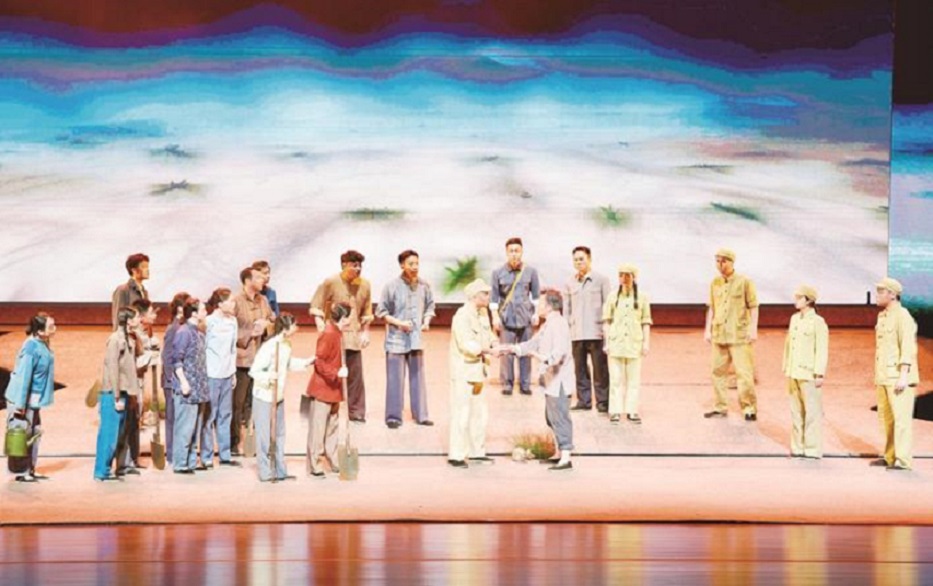
情景党课《人民公仆谷文昌》剧照
我在东山县谷文昌纪念馆看到了这一段记载,百感交集。陈列橱窗里还有当年项南书记亲自修改并决定发于《福建日报》第一版显要位置的一篇带图片的新闻稿。该文稿发表于1981年2月2日的《福建日报》上,是当年介绍谷文昌事迹、提倡向谷文昌学习的一篇重要文章。这是我记住的关于谷文昌的最早一篇文章,对我而言它是一个寻找的起点,我从这里开始寻找一个人的足迹。
我觉得自己是注定要去寻找。当年谷文昌逝世之时,我与他近在咫尺,却又相当陌生。谷文昌逝世于龙溪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任上,当时我是他的属下干部、地区行署办公室的一个青年干事。我们行署办刚组建不久,包括主任、秘书和干事一共才五人,我是第五个干部,从县里调上来才几个月。我依稀记得在行署曾见过谷副专员,却没有机会接近。他生病住院,而后去世,看到讣告,我才意外发现自己跟这位领导是老乡:谷文昌是河南省林县人,我虽生于闽南,籍贯也是河南林县。
因此我邂逅了一段漫长的足迹,从北国到南方,从中原大地太行山脚延伸到福建南部的东海之畔。当时我虽年轻,对这段足迹背后的历史故事却久已有所了解:解放战争后期,奉中央命令,华北晋冀鲁豫解放区太行、太岳两个地区集中6000余干部,以“长江支队”为番号,于1949年4月下旬从集结地河北武安县城出发,踏上南下之旅,任务是接管素有天堂美誉的苏、沪、杭一带。一个多月后,支队长途跋涉,经南京到达苏州。由于解放战争形势发展迅速,上海于5月中旬解放,华东干部已经接管了苏杭一带,长江支队奉命于苏州待命,7月中旬再从苏州出发,经浙江嘉兴、杭州、江山,徒步翻越浙闽交界的仙霞岭进入福建。长江支队共有六个大队,其中第五大队进军闽南龙溪地区。第五大队辖有五个中队,其中第三中队负责接管龙溪地区的海澄、东山两县,时谷文昌为该中队第五小队小队长。当年9月,五中队到达龙溪地区,隔年5月,解放军渡海作战,解放东山岛,谷文昌与他的战友进入东山,完成他这段历时一年有余漫长的南下历程。
我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最初来自自己的父亲,当年我父亲同样也是循着这条道路从北国来到南方,他是四中队的一员,与谷文昌同属长江支队五大队。长江支队的成员大多是第一次到福建。此前,福建在他们的印象中陌生而遥远,传说中福建山多,虎蛇多,蚊虫多,交通不便,瘟疫流行,有“瘴气”,与他们原定前往的苏杭一带不是一回事。但是使命所系,义无反顾,他们一路南下,来到福建,展开工作,落地生根。长江支队尤其是五大队里的河南林县籍干部不少,到达福建后十数年,他们的家乡以著名的“林县红旗渠”为世人所知。上世纪90年代,林县改称“林州市”。时至今日,他们中的健在者几乎都年逾八旬,有许多人已如谷文昌一样长眠于南国的土地。
作为第二代人,寻找这段历史于我有一种寻根意味,让我充满感慨。我常把历史想象为一位智者,他的一举一动都意味深长。他让谷文昌和我的长辈们远道而来,留下一行漫长的足迹,一定有其用意。也许缘出于此,我发觉自己在记忆中的谷副专员病逝远去后,还一再与之相逢,不断邂逅他留下的足迹。这里有工作的机缘,也因为心之所向。1987年,东山县赤山林场一个面对西浦湾林木葱郁的山头上立起一面“谷文昌同志万古长青”的石碑,东山县委按照人民群众要求和谷文昌生前遗愿,举行庄重仪式,将谷文昌同志的骨灰安葬在那里。谷文昌早在1964年即已调离东山,20多年过去了,为什么会以如此荣誉方式归返于此?一时引发人们注意,我自然也为之心动。几年后,1990年,一部反映谷文昌事迹的电视剧在东山岛开拍,省、市委宣传部领导前往东山看望剧组,我相陪一往。我记得那部电视剧剧本起初曾经叫《外乡人》,描绘来自北国远方的谷文昌在南国海岛东山创业的功绩,寓意颇深。后县、市、省委分别发出通知,号召向谷文昌学习。当时我在漳州市委宣传部工作,见证了那一次学习活动在全市、全省开展全过程,更由于参加谷文昌事迹材料的收集整理,格外深切地感受这一位前辈领导在这一块土地和人们心中留下的深刻印记。
我能感觉到这些足迹之重。当年谷文昌与他的战友进入东山之际,饱受战乱和自然灾害摧残的这个海岛县满目疮痍。东山经历的兵祸可称巨大,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败军祸及全岛,制造了这座岛屿的旷世惨痛,广为人们所知的“寡妇村”为其中突出一例。1953年7月,这座岛屿又成为一大战场,万余国民党兵突袭东山,海陆空协同作战,抢滩登陆,占领县城。东山驻军、民兵和驰援东山的解放军部队与之激战三日,“东山战役”成为海峡战史上著名一战,国民党部队败离东山,却给这座岛屿又添了创痕。除了巨大的战争创伤,东山还为无休无止的自然灾害所苦,海岛缺水,干旱,交通不便,尤其是风沙肆虐,埋屋毁田,为当地大害。谷文昌到东山后先当区委书记,再任组织部长,然后是县长、县委书记。从1950年进驻直到1964年调离,前后14年,他的足迹遍及全岛,在这里抚平创伤,重建田园,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修桥铺路,全面建设。诸多事迹里,最为人称道、至今让人们时时怀念的是他带领东山干部群众“上战秃头山,下战飞沙滩”,植树造林,绿化海岛的事迹。这座海岛从1957年开始大规模造林,到1964年谷文昌调离时,已营造30000多亩防风固沙林,60000余亩水土保持林,林带210条,荒岛变成了“东海绿洲”。与谷文昌所处时代所发生的各重大政治、经济、文化事件比较,种树这种事情称不上惊天动地,但是正是它成为谷文昌的鲜明标志,是他留在这块土地上最深的一行足迹,让人们一再感念,也让我一再寻找,反复思索。
新世纪头一个十年里,我又见证了影响广及全国的新一波学习谷文昌活动,时我已经调到省直单位工作。2003年春,我陪一位老领导再访东山,不久按照上级安排,与本省十数位作家一起采风东山,寻访谷文昌的足迹。我们去了赤山林场谷文昌陵园,当时谷文昌的事迹展览馆还在林场山头的观林楼里,位于其纪念碑和石雕像近侧,谷文昌纪念馆刚在动工兴建。我注意到谷文昌的碑前摆着一只香炉,有一支香烟插在香炉里静静地燃烧,不是民俗中用于上香的那种专用物品,是人们通常所抽的带过滤嘴的香烟。有人用这种方式请谷文昌抽一支烟,以表自己的崇敬与感谢。香炉里的这支寻常香烟让我联想起听到的一句当地俗语“先敬谷公,再敬祖宗”,为之怦然心动。
此时的东山已经满岛绿荫,难觅当年飞沙走石的恶劣景象。看着海滩上成排的木麻黄挡风林,很难想象当年把它们一株株种活有多么艰难。随着时日迁移,环境改变,半个世纪前谷文昌和东山干部群众种树的故事已经渐渐成为一个记载。当年谷文昌他们下决心在荒山沙滩上种树,防沙固沙,但是屡试屡挫,种下的不能活,种活的不能长,几经反复终于找到了适宜在东山沿海环境生产的树种木麻黄,并以一种顽强不息的精神,付出了无数心血与劳动,把它种遍全岛。这些历史记述似乎越来越像一段旧迹,逐渐归入尘封。但是一旦身临其境,站在谷文昌陵园的山头上,看到周边浓绿遍布,记载和旧迹顿时就会活灵活现,让人感受到一种深刻的真切。这时也才特别能够理解,许多远走台湾的东山人,隔绝数十年后终于可以回乡探亲,他们也像一直生活于此间的乡亲一样,到山上敬一敬谷公。为什么呢?记忆中的家乡曾经荒芜,而今一片翠绿,当年这一位共产党的县委书记为此不懈努力,做出开创性贡献,他值得尊敬。
2010年初夏,我参加省炎黄研究会与省作家协会组织的采风活动,再次来到东山。此刻这个海岛热气腾腾,以建设国际旅游岛为奋斗目标,大项目一一上马,道路四通八达,城乡建设蓬勃,势头正旺,迎来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时隔数年重访,在感受巨大变化之际,我再上谷文昌陵园,重寻远去的印记。这里也是新颜,谷文昌纪念馆庄重矗立,周边环境清幽祥和。沿着颇显大气的石阶拾级而上,到了山顶园区,我又看到了记忆中曾让我怦然心动的那个碑前香炉,依然有香烟在香炉里静静燃烧。从山顶近观绿色原野,远眺蓝色海洋,我感觉到一片崭新,同时依然还有一个旧日的足迹隐约显现于崭新之中,悄然无声,融合着昨日与今天。
谷文昌调离此地已近半个世纪,在近30年前那个冬日里于漳州辞世,但是显然他并没有离去。当年他在这里种下防风林,绿化一座海岛,成为今日这里兴建国际旅游岛的一个基本依托;当年他在这里推进的城乡建设和经济发展、成为今日这里跨越式发展的基础与先声;当年他在这里修建学校,培养的孩子成为今日海岛建设的主力;当年他在这里发动群众,建立组织,打造人民政权的政治基础,如今依然是科学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的强大核心。他的足迹因之长留于此。
这只是东山,只是谷文昌吗?当然不是。事实上我所寻找、邂逅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的足迹。谷文昌以及他身边的干部群众,远从北国跋涉而来的长江支队那些“外乡人”,流血牺牲英勇战斗解放福建的解放军指战员,艰苦卓绝坚持斗争的中共福建地下党组织成员,从各个方面汇集在一起的革命者,还有与他们血肉相连的人民,他们共同创造了那个时代。谷文昌是他们的一个代表,那个时代的一个代表,他的足迹是他们的足迹,那个时代的足迹。从那个时代开始,经过了一批批后来者的接续和努力,我们才走到了今天。
我发觉自己与其说是寻找一些远去的足迹,不如说是寻找历史在这些足迹里融进的意义和价值。有些足迹很快就会湮没于岁月的尘土,有的却能长存,一如我所寻找的这些。它们开创了昨日,奠定了今天,是我们创造未来的基础和财富。
(原载于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省作协“走进八闽”文化采风系列之《走进东山》;图片来源于漳州新闻网,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