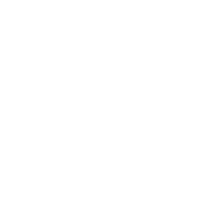挡不住《书的诱惑》
汪毅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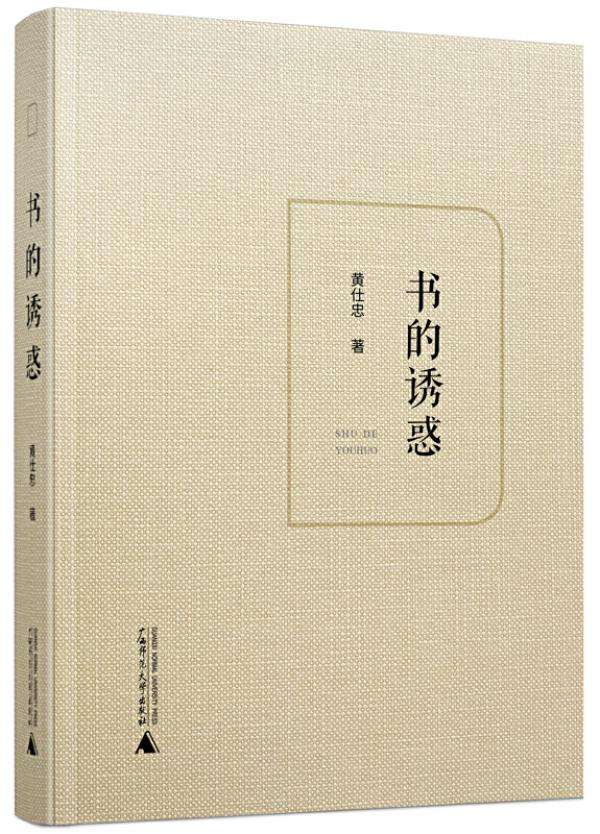
一本关于书的书,“读书种子” 黄仕忠话说读书、教书、写书,借书、淘书、藏书,乃至校书、赠书和卖书的《书的诱惑》,果然是挡不住的诱惑:接到书的一日夜里,我已经读了两遍、想了好多。
黄仕忠教授是广州中山大学的学术牛人之一,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戏曲史研究和教学,成果(包括门下桃李)相当可观,让人好生钦佩。在我看来,做戏曲史研究的人,往往有冷、热两副心肠。台湾学者洪弃生(1867—1929)曾“向友人借得《钧天乐》一部”,并在《阅〈钧天乐〉小柬》说明读古人戏曲宜有的两种态度,一是“宜仔细寻其脉络、玩其结构、赏其雅唱、识其寓言”,这是冷处理: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保持冷静态度、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以做仔细之研究;另一是“要须一部屈子《骚》、马迁《史》,一副嗣宗泪、祢衡口,合作一场鼓吹耳。然又须蓄瓮清浊酒,刮一双青白眼、开一个不合时宜肚,乃得浇泼其积年块垒、发泄皮里阳秋,不然,重负作者”,这是热作业:研究者将个人情感同研究对象混同,来一道热烈的再创作的工序。黄仕忠教授的研究乃臻于更高的境界,他追求的是个人的情感同作为研究对象的“作家的心灵”的“对话”:“当深入某一作家的心灵,便是得到一个永生不渝的知己,静夜之时,每可作心灵的对话”,对话“深入”而不失彼此之分;另一方面,研究者个人情感完全不介入作品研究,他做的版本、校勘、辑佚、考据和目录之类的作品研究是相当冷静而仔细的。
《书的诱惑》里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学术经验。例如,“随徐先生研读《史》《汉》二书,我得到了很好的学术方法训练。后来在研读《琵琶记》时,我发现早期版本与明代以后的版本相较,在文字上有所不同,所以也很自然地选择代表性的版本,做了详细比勘,一一罗列异文,细细体味不同的细节处理在具体演出及刻画人物心理上的差异,体味明人改本在局部场景下对人物心理的新理解、定位,与剧本整体是否相洽。这样多方揣摩,对剧本的理解渐趋深入,慢慢构成对作者整体思路的一种新的理解。又把'原义'与明人依据自身思想观念的要求而增加或强化的那些'引申义'加以区分,从而发现今人对于《琵琶记》负面评价的例子,大多与明人的改动、选择性强化有关。”30年前,我随刘登翰教授等编写《台湾文学史》时发觉,像我这样的中文系(所)出身的学者,因为不曾接受史学学术训练,往往发生史学常识错误。黄仕忠教授的学术经验则从正面证明中文系(所)出身的学者接受史学学术训练的必要性。
从《书的诱惑》可以看到,黄仕忠教授对师辈、同辈和后辈学者的诚挚态度。 师辈在世,当执弟子礼甚恭,却不可对人言必称“吾师”以自炫;及师辈逝去,则当尊师如师在,常语人曰“我的老师”以志师恩并记学术传承也,代代学人皆当如是。我曾到中山大学,亲见黄仕忠教授的团队亲密合作、承王季思教授而来的中国古代戏曲史研究的学术传统延伸于不墜的情形,心里很是感动。
《书的诱惑》里有许多事关学界的趣闻和谈资。如,黄仕忠教授考取杭州大学硕士时,“专业课成绩是60分。事实上古代文学专业同届的五位同学,入学时的专业成绩好像都是60分”,“这大约是杭大先生的习惯”。这让我记起,我考福建师大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硕士时,基础课古代文学考题有一道论述题:“《清忠谱》的作者是谁?请简要论述《清忠谱》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要命的是,这道题占分百分之四十。我勉强答了一些,如“事俱按史”、“群众斗争场面”之类,这一门基础课考了60分。出题的陈教授说:“如果连这样的题也不会,还考什么研究生”。老先生说得好,对学生当有“60分”的基本要求。但“先生们的习惯”于今似乎不被强调了。
附带言之,《书的诱惑》是2020年1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刚出炉的,好着呢。
(作者汪毅夫系厦门大学讲座教授、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