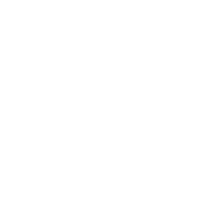鲁迅如何批驳“男尊女卑”的“特色理论”
宋志坚

鲁迅画像
在“男尊女卑”的时代,很难有纯正的男女情爱。所谓“男女大防”,“防”的往往只是女人,她们只是男人的附属品,不能在男女之礼上越雷池半步。男人在占有她们的时候,性欲多于情爱。男人可以有三房四室,女人不乏贞洁牌坊。纯正的男女情爱,往往成为礼教束缚下的撕心裂肺的人间悲剧。这是男权社会的必然结果。
于是,在中国几千年“男尊女卑”的社会中,就有种种“特色理论”:
“女祸论”,也就是“女人亡国论”。夏商周三代都有实例。“妹喜有宠”而“亡夏”,“妲己有宠”而“亡殷”,“褒姒有宠”而“亡周”。此“宠”乃宠物之“宠”。无论妹喜、妲己还是褒姒,这些原先“在河之洲”的“窈窕淑女”,都不过是充当了男人的“宠物”而已。宠者沉迷于女色而荒废朝政,其罪却得被宠者来承担,这便是男尊女卑社会的一种“特色理论”。就是武王姬发讨伐商纣王的《牧誓》,引的古人之言也是“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说纣王之首恶是“惟妇言是用”。所以鲁迅说,“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的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男子既然不负责任,又不能自己反省,自然放心诱惑;文人著作,反将他传为美谈”。鲁迅1936年2月发表在上海《海燕》月刊上的《阿金》一文中,也说到类似的意思:“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可见在这一点上,鲁迅的观点是一以贯之的。
“贞洁论”,此“贞”乃坚贞不渝之贞,“贞”而方可称之为“洁”。只就“爱情”二字而言,坚贞不渝本就应当是对男女双方的共同要求。但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中,“贞洁”只是对女子而言,女子未婚应当守身如玉,已婚更应从一而终,这是“妇道”的主要内涵。男子似乎从未有过“贞”与“不贞”之说,即使确有“不贞”,也不会有人称之为不“贞”,更不会有人称之为不“洁”。不仅如此,即使男人诱惑以至强暴了女子,这不贞不洁的恶名也与男人无关,反要女子承担。鲁迅称这种“特色理论”为“只有自己不顾别人的民情,又是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造出的“畸形道德”,这种“畸形道德”,“主张的是男子,上当的是女子”。
“节烈论”,这是“贞洁论”的最高形态。“节”是节操之节,气节之节;“烈”是壮烈之烈,烈士之烈。这本来也是无论男女皆可能因为自己的付出或牺牲而获得之殊荣。然而,当“节”与“烈”捆绑在一起之后,就属女子所独有了——丈夫或未婚夫死了,决不再嫁或私奔,称之为“节”;丈夫或未婚夫死了,跟着一起死去;或遭遇色鬼强暴,以自戕守身,因抗拒被杀,都可称之为“烈”。反正是要女子为丈夫或未婚夫活着守寡或死去尽忠的。
对于这种种“特色理论”,鲁迅都曾有过针锋相对的批驳,在《我之节烈观》一文中批驳得尤为集中。他以“旧时的常识”与“略带二十世纪的气息”两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层层质疑。
倘按“旧时的常识”,鲁迅的质疑有三。一是“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鲁迅说,当时的“国将不国”与“种种黑暗”,“竟和古代的乱世仿佛”,然而,“政界军界学界商界等等里面,全是男人,并无不节烈的女子夹杂在内。也未必是有权力的男子,因为受了他们蛊惑,这才丧了良心,放手作恶。至于水旱饥荒,便是专拜龙神,迎大王,滥伐森林,不修水利的祸祟,没有新知识的结果,更与女子无关”;二是“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鲁迅说,“照着旧派说起来,女子是‘阴类’,是主内的,是男子的附属品。然则治世救国,正须责成阳类,全仗外子,偏劳主体。决不能将一个绝大题目,都阁在阴类肩上。倘依新说,则男女平等,义务略同。纵令该担责任,也只得分担”;三是“表彰(节烈)之后,有何效果”?鲁迅说,已经守节的,正蒙表彰,不必说了。不守节的,不值得说了。只剩下丈夫尚未死去的,你让她们都打定主意,“‘倘若将来丈夫死了,决不再嫁;遇着强暴,赶紧自裁!’试问如此立意,与中国男子做主的世道人心,有何关系?”
倘若“略带二十世纪气息”,鲁迅质疑有二。一是“节烈是否道德”?鲁迅说,“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而“现在所谓节烈,不特除开男子,绝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体都遇着这名誉的机会。所以决不能认为道德,当作法式”;二是“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鲁迅说,“社会国家,又非单是男子造成。所以只好相信真理,说是一律平等。既然平等,男女便都有一律应守的契约。男子决不能将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别要求”。这后面一条,其实还无须“略带二十世纪气息”,按照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应提出质疑。
《我之节烈观》对上述“特色理论”或“畸形道德”的批判,并没有“一锅煮”。鲁迅回顾了从夏商周直到清代这三千年中,形成这些“特色理论”或“畸形道德”,尤其是所谓“节烈”的历史过程:
中国太古的情形,现在已无从详考。但看周末虽有殉葬,并非专用女人,嫁否也任便,并无什么裁制,便可知道脱离了这宗习俗,为日已久。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的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看见历史上“重适”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出于真心,还是故意,现在却无从推测。其时也正是“人心日下,国将不国”的时候,全国士民,多不像样。或者“业儒”的人,想借女人守节的话,来鞭策男子,也不一定。但旁敲侧击,方法本嫌鬼祟,其意也太难分明,后来因此多了几个节妇,虽未可知,然而吏民将卒,却仍然无所感动。于是“开化最早,道德第一”的中国终于归了“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的什么“薛禅皇帝,完泽笃皇帝,曲律皇帝了。此后皇帝换过了几家,守节思想倒反发达。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愈加利害。看见唐人文章里有公主改嫁的话,也不免勃然大怒道,“这是什么事!你竟不为尊者讳,这还了得!”假使这唐人还活着,一定要斥革功名,“以正人心而端风俗”了。
按照上面所述,“节烈”的始作蛹者乃是宋代的“业儒”,尤其是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家程颐,从那之后,越演越烈。鲁迅没有将这笔账全都算到儒宗孔夫子的头上。当然,倘若追溯上去,提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并将女子打入另册的孔夫子似也难辞其咎。
但从上述引文中,也可以看出,从孔子算起的儒家“男女”观之流变,尤其是“节烈”的形成风气,大致得力于这样两个方面:
首先是得力于权势。“三纲五常”是董仲舒提出的,但没有汉武帝的首肯,恐怕也难以推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程颐的主张,倘若无益于权势,也成不了气候。“三纲五常”之“三纲”本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虞翻对孙权说:“臣闻周公制礼以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同措)’,是故尊君卑臣,礼之大司也。”与此相应的,便是尊父卑子,尊夫卑妻。那么,“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皇帝换过了几家,守节思想倒反发达”,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历朝历代,大凡“表彰节烈”的,都是“政府行为”,以至于直到1914年,想做皇帝的袁世凯还要“表彰节烈”。
同时也得力于业儒。鲁迅说:“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利害。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将“妇”解释为“服也”的《解文说字》之作者许慎,也是汉朝的“业儒”。这个“服”字,便是征服、训服、压服之“服”,民间还将其读为衣服之服,所谓“兄弟是手足,夫妻是衣服”是也。此处且不说汉儒宋儒,只说鲁迅在上面那段话中提到的“愈加厉害”的清儒,对于劝导妇女的“节烈”,也是动过许多脑筋,编过许多故事的,各种各样的都有。鲁迅先生说:“只有说部书上,记载过几个女人,因为境遇上不愿守节,据做书的人说:可是他再嫁以后,便被前夫的鬼捉去,落了地狱;或者世人个个唾骂,做了乞丐,也竟求乞无门,终于惨苦不堪而死了!”这“说部书上”记载过的“几个女人”,即“女人再嫁后遭遇惨苦的故事”,《鲁迅全集》注释中就有二例。一是清代百一居士所作之《壶天录》,二是清代俞樾所作之《右台仙馆笔记》中的《山东陈媪》条,看过此二例者,就不难理解,鲁迅为什么会说“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愈加利害”了,甚至还可由此想到鲁迅在此六年之后所写之短篇名著《祝福》中的祥林嫂。我想,早在写下《我之节烈观》之时,鲁迅或许已经萌生了要写祥林嫂这个悲剧人物的念头,甚至也已经闪现了“重适”的祥林嫂因为担心到阴司去后灵魂被阎王分锯而去土地庙捐门槛的意象。所谓封建礼教吃人,此之谓也。
鲁迅的《我之节烈观》,不仅是历史的清算,更是现实的抗争。他写此文,就是针对袁世凯颁布《褒扬条例》,规定“妇女节烈贞操,可以风世者”,给予匾额、题字、褒章等奖励,以及报刊上颂扬“节妇”、“烈女”的纪事和诗文等情况,作出的批判,具有非凡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