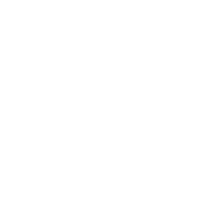鲁迅“一个都不宽恕”的是些什么人
鲁迅遗言“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此中的“他们”指的是谁?
指的是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等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文学”家吗?显然不是。尽管这些“革命文学”家对于鲁迅的批评,调子定得很高,什么“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法西斯蒂”等等,简直罪不可赦,火力也相当密集,可谓四面埋伏,轮番作战,几成“围剿”阵势。对于他们,鲁迅曾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针锋相对,毫不含糊。然而,以后毕竟在同一目标之下,彼此和解了的。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中,也曾说过:“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这“未尝一面”而“曾用笔墨相讥”的,说的就是郭沫若,或许也包括创造社与太阳社中的别的人物,这就双方而言,乃是一种和解:从鲁迅的角度说,便是一种宽恕。
指的是钱玄同、林语堂、周作人等曾经与他相知相伴尔后相离以至于有笔墨相讥的亲朋好友吗?同样不是。我曾在谈及鲁迅与孙伏园的“后期疏远”时,说到鲁迅性格上的欠缺。我以为这种性格上的欠缺大致有三:其一,他以十分的真诚对待别人,也要求别人以同等的真诚回报于他,一旦发现别人对他未必就有那样的真诚,心中便有老大的不快;其二,他与甲为友,与乙为敌,便希望甲以他之敌为敌,一旦发现甲与乙有来往,心中也有老大的不快;其三,他与别人有隔阂之后,不善于主动地去弥补这种隔阂,也不轻易谅解别人的过错。这三条,或许也可称之为人性的弱点,在不少人身上均可看到。(参见拙著《鲁迅根脉》下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1月版)从钱玄同、林语堂在鲁迅身后所写之纪念文字中,也可看到类似的意思。然而,对于这种原先相知相伴后相离的人,鲁迅心中是有隐痛的。仍以孙伏园兄弟为例:1929年3月20日《鲁迅日记》中记着“伏园,春台来”,这该是孙氏兄弟赴欧洲前向先生辞行;1929年4月13日《鲁迅日记》中记着“上午得孙伏园等明信片”,这该是孙氏兄弟到达欧洲后向先生报平安,这点点滴滴的记载,本身就体现着鲁迅对他们的宽恕。我以为,鲁迅对钱玄同、林语堂以至于周作人,也有类似的心绪。胡兰成致朱西宁信中转述“战时”许广平在上海对他说的一句话:“虽兄弟不睦后,作人先生每出书,鲁迅先生还是买来看,对家里人说作人先生的文章写得好,只是时人读不懂。”舒芜先生认为胡兰成的转述“夸大其词”,因为他在《鲁迅日记》附录的“书账”中只看到“周作人散文抄”和“看云集一本”这两条(《文汇报》2007年11月8日),但舒芜先生忽略了,鲁迅所买的周作人的不少书,并不进入他自己的书账,只在《鲁迅日记》中记着“为广平买”或“为广平补买”,这是很能体现其相当复杂的情感的。这种情感,并非“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可以取代。
那么,鲁迅“一个都不宽恕”的“他们”中,到底有些什么人?
鲁迅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显然,他“一个都不宽恕”的不是“论敌”,而是“怨敌”。
对于依仗权势欺压弱者被他抨击而怨恨他的人,他是不会宽恕的。例如,拿着教育部为“防止学生上街流行”的鸡毛当令箭,以此来压制本校学潮,不惜借助于警察与武力来压制莘莘学子,假借“评议会”之名,开除在女师大风潮中为首学生的校长杨荫榆,例如,充当杨荫榆的后台,为杨荫榆弹压学生撑腰,滥用职权撤销因为支持女师大学生的鲁迅教育部佥事之职务,甚至以“不受检制”、“蔑视长上”为借口,下令解散“女师大”的教育总长章士钊,等等。鲁迅更不会宽恕血腥镇压学潮,制造3·18惨案的段祺瑞执政府,要不,他就不会说3·18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要不,他也不会写下:“血债要用同物偿还,拖欠得越久,便要付出更大的利息。”同样,鲁迅也不会宽恕日后那些“杀人如草不闻声”,制造一个又一个血案的新贵,他的《为了忘却的纪念》等文章,吐露的或许就是这样的心迹。
对于那些貌似公允,满口公理,却明里暗里充当权势者的帮凶或帮闲的角色,那些“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的人”,他是不会宽恕的。例如,在“女师大风潮”中说“闲话”的“正人君子”陈西滢,对于“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说是赤化,是共产……甚至于到官里去告密”的角色,他是不会宽恕的。例如,写文章暗示别人“拥护苏联”和“到××党去要卢布”的梁实秋,鲁迅在那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就说得明白:“为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得合时,或者还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此类人中,还包括向官府告密而让他们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的许绍棣叶溯中与黄萍荪等人。鲁迅常常称这种权势者的帮凶或帮闲为“叭儿”,他在《关于许绍棣叶溯中黄萍荪》这篇短文中就曾这样写道:
当我加入自由大同盟时,浙江台州人许绍棣,温州人叶溯中,首先献媚,呈请南京政府下令通缉。二人果渐腾达,许官至浙江教育厅长,叶为官办之正中书局大员。
有黄萍荪者,又伏许叶嗾使,办一小报,约每月必诋我两次,则得薪金三十,黄竟以此起家,为教育厅小官,遂编《越风》,约“名人”撰稿,谈忠烈遗闻,名流轶事,自忘其本来面目矣。“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然一遇叭儿,亦复途穷道尽!
鲁迅不会宽恕的,还有一种人,就是“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并以“鸣鞭为唯一业绩”的“奴隶总管”了。他对这类人的厌恶,其实并不亚于他的“怨敌”。这种厌恶情绪,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
就像孔子的宽恕不是绝对的一样,鲁迅的不宽恕也不是绝对的。以上所说的这一切的“不宽恕”,都有一个界限,就是“改而止”。所以,假如鲁迅知道日后杨荫榆保持民族气节,惨死于日寇之手,假如鲁迅日后知道章士钊仗义出庭为陈独秀作法律辩护,如此等等,则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