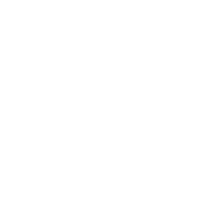严译《中国教育议》之主旨与价值
薛 菁
《中国教育议》是严复于1914年3、4月发表于梁启超主办的《庸言》报第27、28期的一篇译文,原作者是犹太裔德国人卫西琴博士(Dr.Alfred Westharp),该文“以救一国之亡”而作,与严复“所求”甚为契合,所谓“卫君愿宏,若仆之所求”。[1]这就是严复翻译此文的动因。
一、卫西琴其人
卫西琴,原名Victor Egon Frensdorf,是20世纪德国颇具传奇色彩的教育家、心理学家和音乐家。他的英文名是Alfred Westharp,harp在英文里意思为竖琴,竖琴是西洋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所以Westharp直译为“西琴”,又取姓氏开头音节we,音译为“卫”,因此其中文名为卫西琴。卫西琴1882年出生于德国柏林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7岁上大学。1907年,他在慕尼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主修音乐学和心理学。此后,他先后前往法国、英国,投身于人类心理和教育问题的研究。旅法期间,他接触到《中庸》《论语》等儒家经典,感受到东方文明的魅力。在英国,他学习了意大利教育家玛利娅桔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1870—1952)的教育心理学相关理论。1913年4月,出于对中国儒家文化的倾慕,卫西琴抵达上海。在上海,他发现中国从服饰、建筑到教育、音乐等都在盲目模仿西方,而他在欧洲感受到的中国固有的文化和精神却无处可寻。两年后,他带着失望离开上海前往日本。在日本,他观察到的情形与在上海时大同小异,都是对西方的拙劣模仿。为此,他再度来华,怀着“救一个国家”的愿望发表了几篇长文,其中就包括《中国教育议》,还为自己取名“卫中”,意为保卫中国文化。
《中国教育议》的核心观点就是极力反对中国教育模仿欧洲现行的“死法教育”,主张中国建立独立的教育系统,并将教育独立视为国命之所系。在卫氏看来,蒙台梭利的教育心理学与中国儒家经典“尊崇自然”“成己成物”的内容不谋而合,“中国之民性,固不必借径于欧洲之旧法教育,凡学必由心识而后为躬行。但用蒙氏之教育术,自可立致知行合一之妙,本于由成己者而为成物”[2]。因此,他建议中国教育改良可以以孔子的“心理学”为“中国固有的心理学”,再通过“蒙台梭利之方法”发展中国人的身体能力,最终达到精神与物质大通的自然境界。[3]他甚至认为“在中国文化中存在着解决西方现代性弊端的办法”[4] 。
他所发言论多是情不自禁的直抒胸臆,国人乍闻其言,相视诧讶,或疑其是疯子,或疑其是骗子。他投书严复,希望严复能把自己的著作翻译发表,严先生对其文稿多日未加展阅,更未置答。卫感到极度失望,几无可与语者。正当他准备离开之际,严复忽来信挽留,表示欲翻译其文《中国教育议》。译文在《庸言》报刊出后,《湖南教育杂志》《云南教育杂志》、杭州《教育周报》等相继转载,一时间,卫西琴在中国思想界、教育界“颇为士林瞩目”。正如梁漱溟所言,“国人之知(卫)先生者,大抵以侯官严先生所为译《中国教育议》一文”[5]。
之后经严复推荐,卫西琴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多次演讲,并与社会名流多有交往,但未能引起足够重视,他便前往保定教音乐。1919年10月,时任保定高等师范学校音乐教员的卫西琴率师生赴晋,为在太原召开的第五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大会演奏《诗经》的乐章。此举颇具反响,山西省省长兼督军阎锡山深知卫西琴的名望,更因卫氏宗圣东方儒学、推崇孔子之道与其“中庸”“忠君”“尊孔”的统治理念一致,于是邀请卫氏到太原任教和办学。自1919年底至1925年底,卫西琴先后在山西大学、国民师范学校和外国文言学校任教长达六年之久。尤其是其接办外国文言学校,以卢梭、蒙台梭利等西方启蒙教育家的思想为宗旨,注重培养学生的自由发展意识和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他还自编教材,开设国文、史地、生物、心理、教育、音乐、体育等课程,又设置校办工厂、校办商店及农艺园地,培养学生全面发展。他的这些别具一格的教学方法引起全国教育界的关注,“其间所有,举不同俗,一事一物,靡不资人省味,顿为惊叹。……学生百数十人,颜色泽然,神采焕然;凡外间一般学校学生,所有憔悴之色,沉闷之气,于此绝不可见。”[6]然而,由于他的著作理致幽深,意义多半晦涩难懂,用词造句亦不合于通常中国语文,加之他“不谙中国风情,往往措施失当”,因此在学术上曲高和寡,1925年底便离开山西前往北京。
值得一提的是,卫西琴在主持山西外国文言学校期间,与梁漱溟相识,至为投契。到北京后,又与梁漱溟等人在西郊大有庄租房,同住共学,研讨儒家哲学与心理学。经过一年相处,梁漱溟对卫西琴的学问、为人有了进一步了解,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卫西琴成为梁漱溟唯一的外国朋友。而卫西琴在太原外国文言学校的教学实践,启发了梁漱溟后来主张的“乡村建设”,无论是在河南参与筹办村治学院,还是在山东邹平开展乡村建设事业,梁漱溟的许多具体做法都有山西外国文言学校的影子。1927年,梁漱溟应李济深之邀赴广州办学。翌年,他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聘请卫西琴负责高中师范班的工作,与他一起从事“乡治实验”。大概就在这个时期,卫西琴又改名为傅有任,意为对改造中国教育负有责任。“乡治实验”失败后,卫西琴于1931年离开广东,辗转各省演讲,但多客居上海,上海许多报刊频频登载他的演讲内容及相关报道。1933年他申请加入中国国籍终获批准。1938年他离开中国前往日本。
卫西琴在中国生活的25年间,先后在山西、广东进行教育实践,并与许多社会名流有交谊,除梁漱溟、严复外,还有梁启超、张謇、蔡元培、胡适、黄炎培、陶行知、熊十力、吴宓、徐志摩、李四光、梅兰芳、太虚法师等,也为民国时期的一些政要如熊希龄、阎锡山、李济深、陈铭枢、白崇禧、汪精卫等充当过智囊和顾问。他的著作及其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不仅在民国初期产生重大反响,而且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二、严译《中国教育议》之主旨
严复在卫西琴的《中国教育议》“按语”有云:“吾与卫君,始不相识也,近者来见,辞气烦冤,谓其怀来,将以救一国之亡。……一日晨起,取其《教育议》而读之,愈读乃愈惊异。其所言虽不必尽合于吾意,顾极推尊孔氏,以异种殊化,居数千载之后,若得其用心。中间如倡成己之说,以破仿效与自由,谓教育之道,首官觉以达神明,以合于姚江知行合一之旨,真今日无弃之言也。……其言虽未必今日教育家之所能用,顾使天下好学深思之人,知有此议,以之详审见行之法之短长,其益吾国已为不少。孟德斯鸠不云乎:立宪之民,不必其能决事也,但使于国事一一向心脑中作一旋转,便已至佳。”[7]
由此可见,严复翻译《中国教育议》的主旨有两点:
一是复兴孔子之道。
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迎来了第二次科技革命浪潮,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掀起了重新瓜分殖民地的狂潮,原有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被打破。随着各帝国主义国家在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和争夺殖民地问题上矛盾的激化,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战争促使严复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对西方文明重新认识与评估。首先,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文明“尚武爱国,各奋其私”的产物。他说:“欧罗巴之战,仅三年矣,种民肝脑涂地,身葬海鱼以亿兆计,而犹未已。横暴残酷,于古无闻。兹非孟子所谓率土地以食人肉欤!则尚武爱国,各奋其私,不本忠恕之效也。”[8]其次,在中西对比中他感觉到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界可能显现新的价值,中华文化终将有大放光彩之日。他说:“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他借英人之语重申了自己这一观感:“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英前外相葛黎谓:此战若不能产出永远相安之局,十年后必当复战,其烈且必十倍今日,而人种约略尽矣!英国看护妇迦维勒(Miss Cavell)当正命之顷,明告左右,谓:‘爱国道德为不足称,何则?以其发源于私,而不以天地之心为心故也。’此等醒世名言,必重于后。政如罗兰夫人临刑时对自由神谓:‘几多罪恶假汝而行也。’往闻吾国腐儒议论谓:‘孔子之道必有大行人类之时。’心窃以为妄语。乃今听欧美通人议论,渐复同此,彼中研究中土文化之学者,亦日益加众,学会书楼不一而足,其宝贵中国美术者,蚁聚蜂屯,价值千百往时,即此可知天下潮流之所趋矣。”[9]因此他说:“我辈生为中国人民,不可荒经蔑古,固不待深言而可知。盖不独教化道德,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之本原。乃至世变大异,革故鼎新之秋,似可以尽反古昔矣。然其宗旨大义,亦必求之于经而有所合,而后反之人心而安,始有以号召天下。”[10]1921年他临终之际,不无遗憾地说:“徒以中年攸忽,一误再误,致所成就,不过如此。”另外,他还重申了自己的文化立场:“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11]
与此同时,国内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1912年,在教育部“学校不准读经、不准祀孔”的规定下,南方许多学校纷纷废除了尊孔读经的常例。一时间,全国掀起了一场荒经蔑古之风,传统文化遭遇边缘化,康有为1913年在《孔教会序二》中直言:“一切文明,随之而尽也,即一切种族,随之而灭也。”严复对此忧心忡忡,甚至感到困惑与不安,他看到了中国即将失去“自我”、失去“国性”的苗头,因此,卫西琴将自己主张融合中西的《中国教育议》奉送至严复眼前,严复“愈读乃愈惊异”。1912年11月,康有为、陈焕秉、沈曾植等人以“挽救人心维持国运”为宗旨成立了孔教会,得到了王恺运、孔令贻、李佳白、卫西琴等中西学者的响应,严复名列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严复这一时期对孔教的支持并非纯粹地希望回到保守状态,而是希冀以此弥补中西学失衡的现象,稳定社会状态。
二是立中国教育之道。
据严复案语,原作者卫西琴撰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救一国之亡”,这里的“国”自然指中国。卫西琴本人于1916年12月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演讲亦说:“中国又正在最悲惨之时,故亦谓为中国悲惨之教育也。”他希望这本书能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严复译之,未尝不是因为其救国属性。
严复在《中国教育议》开宗明义曰:“中国此后教育方针,所宜详明讨论,当事者亦所深知。盖此后中国国命纯系教育问题,人而知之,已无疑义。且所谓问题,非指泛常教育而言,乃问中国此后教育能否自成独立统系,抑从日本之后,事事以仿效欧美为能。”[12]严复希望《中国教育议》的内容能成为中国今后的教育方针,不再走过去事事模仿西方的老路,而是要建立一个中国自己的、独立的教育系统。
1914年,易白沙发表在《甲寅》杂志的长文《教育与卫西琴》一文中说道:“严氏译其文,欲以定今日教育之指针,则严氏已极惊伟,叹为岐山之凤音。鼓舞之情,流露于译文,殆禹闻善言则拜之意也。”易白沙的这句话有两层含义:其一,他明确说明了严复翻译《中国教育议》的目的是定下中国的教育方针;其二,他看完译著之后,以“岐山鸣凤”说明严复十分认可卫西琴的教育思想。接着,易白沙又说:“虽然,卫氏之言因全国上下心理之趋向而言者也,严译亦因全国上下心理之趋向而译者也,言者译者既合于全国心理之趋向,其影响所及,可以推知政府更将持之有故。”这句话也清晰表明了严复翻译此书顺应了全国民众的心理,依据民情而译。可以说,严复翻译《中国教育议》最主要的目的是借此制定适合中国国性民情的教育方针。
因此,卫氏将《中国教育议》托予严复,可谓恰逢其时,适得其所。
三、严译《中国教育议》之价值
从前引严复《中国教育议》序言中可知,严复翻译卫西琴的书,希望达成以下目标:倡成己,破仿效;尊孔;知行合一;复兴中国。此亦为严译《中国教育议》之价值。
第一,建立中国教育系统。
如前述,严复在《中国教育议》的正文中说:“中国此后教育能否自成独立统系?”接着,他例举印度和日本教育状况说明教育独立之重要性。
 他认为印度虽长期为殖民地,但在教育上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系统。究其原因,印度人清醒地认识到“舍己国所本有而取之欧,如是交易,所得不偿所失”,欧洲在体育上存在诸多弊端,体操和美术更是“致少年人有物质功利之思想,而无灵魂”。因此,印度在保持自我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立的教育系统。严复以印度为例,告诫时人“纯用他人学术,利少害多,欲求独立之规,必当更求良法”[13]。
他认为印度虽长期为殖民地,但在教育上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系统。究其原因,印度人清醒地认识到“舍己国所本有而取之欧,如是交易,所得不偿所失”,欧洲在体育上存在诸多弊端,体操和美术更是“致少年人有物质功利之思想,而无灵魂”。因此,印度在保持自我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立的教育系统。严复以印度为例,告诫时人“纯用他人学术,利少害多,欲求独立之规,必当更求良法”[13]。
严复同时还谈到日本过度欧化的问题。他指出,日本的教育几乎全盘仿效德国,缺乏创新。其乖张的教育政策,扭曲了日本人的心理,导致官员利欲熏心,学生只顾利己。基于此,严复总结道:“受病之原,即坐教育法门,无自主独觉之立地。”若想“获东西教化最良之结果”,根本方法是参考印度的方法对“古校之根本义法而改组之”。[14]为了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严复提出新的改革方案:“多购欧美近世教育大家新著之书,而选派东方名宿硕师,使议独立教育之统系,此不独较无危险,即其靡费,亦当较廉。”[15]他主张教材上可择优选取西方的新书,师资上选用中国学贯中西的人才,以此成就独立的“中国教育系统”,此即“倡成己,破仿效”。
第二,主张“以儒为国教”。
针对民国初年中国传统文化遭遇的危机,严复在《思古谈》中说道:“吾国向者以笃故称五洲,而今之后生言维新者,咸以为耻。摧剥戟诟,其志非尽祛古物,若无以与人格也者。故今之时,号曰革命,又曰新世。”又说:“古物之所以珍,而人心之所以笃故,亦自有说。”[16]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历久弥新,自有其存在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教育议》的按语中,严复尤为强调尊孔。“中国之中,有最为中国者焉,曰孔夫子”[17],在他看来,孔子是最能代表本民族文化的典范。因此,他主张以道德(孔子之道)为法律,平衡群己之间的利益关系,维持社会的天然道德。他甚至主张“中国宜以儒为国教,而国民教育统系,宜以孔道为干城”[18],中国文化之珍贵、之价值将会成为“天下潮流之所趋”。
第三,会通中西,知行合一。
严复在改革北京大学教育的时候曾说:“惟既为大学文科,则东西方哲学、中外之历史、舆地、文学,理宜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19]事实上,“兼收并蓄,广纳众流”的主张贯穿严复整个教育思想,而这一主张恰恰与卫西琴的“中西汇合”思想不谋而合。
在《中国教育议》中,严复指出中国如孔子、老子等神明之要道富足,但美中不足的是缺乏物质之学;西方则反之。他指出:“吾辈言教育,视神明之独立,其重要乃如此中国教育家乎?苟欲用国力于至当之地,计惟有取助他山,以建立此不倚之统系耳。”[20]这句话与他1903年所说的“借鉴他山,力求进步”是一个意思,亦与其1917年所说的“惟须改用新式机器掘淘炼而已”有异曲同工之处。由此可见,严复始终在寻求建构会通中西之中国近代教育体系。他认为东西文明“合而为中国之教育,而通国之神明,从此为无疆之进耳”。要做到中西会通,则要先做到“成己”(即保持其自身的天分),对西方文明要选择性吸收,“宜取其偏而不用其全”。
此外,严复主张“知行合一”。早在1907年,他提出中国教育的两大弊端:“今自愚见言之,中国教育,其短有二:一是注重德育而不得其术;二是专重读书,而不识俯察仰观。”[21]他指出,中国的德育必须辅以智育而后知行有合一之日。从《中国教育议》案语“合于姚江知行合一之旨,真今日无弃之言也”来看,严复十分支持卫西琴“知行合一”的主张,赞赏他将西方教育实践与中国神明理论相结合的方法。
第四,复新“大国之风”。
严复在《读经当积极提倡》中强调传统文化“不独教化道德”,还有更为宏大的作用:“世变大异,革故鼎新之秋,似可以尽反古昔矣……而后反之人心而安,始有以号召天下。”“至于人之所以成人,国之所以为国,天下之所以为天下,则舍求群经之中,莫有合者。”[22]由是观之,不难发现严复强调的是传统文化对安定人心、稳定国家、号召天下的作用。他试图通过教育改革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长远目标,换言之,严复早已将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寄托于教育。这种价值理念在《中国教育议》中尤为明显。
严复认为教育是“修身之本”。他说:“至于孔子,又无事此。其言师道,自成而外,无他术也。故曰: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曰修己安人,其贯彻交通而不相抵牾如此。此孔门之名学也。”[23]
严复认为教育是“国命所系”。他在正文的第一段即指出“盖此后中国国命纯系教育问题,人而知之,已无疑义”。他甚至以此告诫中国教育会,提出教育方针:“中国后来之国命,纯视中央教育会诸公眼光之何如。……以公等但知趣过目前,而未尝一为后日中国之长计故耳。”[24]在这里,严复把教育当作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手段。为此,他提出“复新中国”,即“将西人所指之生理事实列之,以供东人之研究,则所以复新中国之图,亦可以得其概矣”[25] 。
严复认为教育可以“拯人类于无穷”。他指出:“尚庶几中国复其本来而为独立之教育,而泰东西合为教化,于以拯人类于无穷。”[26]他回顾了中华民族以往以“自重”的大国之风享誉天下,不幸的是,自重之风在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的接连打击下一扫而尽。诚如上文所引,严复“兼收并蓄,广纳众流”的主张背后是“以成其大”的理想。他援引《中庸》之语表明自己的终极关怀:“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27]
综上,严译《中国教育议》与20世纪初期严复思想转变息息相关,严复通过翻译《中国教育议》阐明自己的教育改革理念,尝试建立一个独立的、会通中西的“中国教育系统”,与其一以贯之的思想抱负和救国主张是一致的,对今日之教育改革亦具启示和借鉴价值。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2025年第6期,作者为闽江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注:
[1][7][12][13][14][15][17][18][20][23][24][25][26][27] 严复:《卫西琴Dr.Alfred Westharp中国教育议》(译者案),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五,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568-569页、第568-569页、第569页、第569页、第571页、第572页、第579页、第570页、第574页、第581页、第575页、第574页、第591页、第582页。
[2]卫西琴著,严复译:《中国教育议》,《庸言》第2卷第4期,1914年3月,第7页。
[3]参见邱念洪:《新旧之间:卫西琴在民初思想界的浮沉》,《中国近代史》2024年第4期。
[4]邱念洪:《卫西琴与民国的反省现代性思潮(1913-1938)》,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
[5]梁漱溟:《〈卫中先生自述〉题序》,《晨报副刊》1926年3月3日,第5页。
[6]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梁漱溟全集》(第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01-802页。
[8]严复:《清诰授光禄大夫太保陈公暨德配王夫人七十寿序》(1917年),《严复全集》卷七,第497页。
[9]严复:《与熊育锡书》,《严复全集》卷八,第365、364页。
[10][22]严复:《读经当积极提倡》,《严复全集》卷七,第463页。
[11]严复:《遗嘱》,《严复全集》卷七,第520页。
[16]严复:《思古谈》,《严复全集》卷七,第443页。
[19]严复:《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贴》,《严复全集》卷七,第403页。
[21]严复:《丙午十二月廿三日在上海华童学堂散学演说》,《严复全集》卷七,第2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