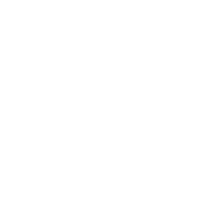绿宝石上的一滴蓝
陈志铭
有一片蓝色水域,镶嵌在我人生的记忆里,它原叫“筼筜港”,后称“筼筜湖”。
“筼筜渔火”曾是厦门八大景之一,那时筼筜港是美丽港湾,每当夜幕降临,渔舟唱晚,渔火点点闪烁,犹如繁星掉落海面,天上人间相互辉映,如诗如画,似梦似幻。少年时代,我曾到筼筜港豆仔尾讨小海。讨小海要根据农历计算水时,在退潮时进行。滩涂海泥细腻如膏,小螃蟹横行,弹涂鱼跳跃,一有动静它们都会在瞬间钻进洞里;海蚯蚓、海蜈蚣是钓鱼的饵料;许多小螺,最多的是织纹螺,它们在海泥上爬行,慢慢吞吞,束手就擒,偶尔还可以见到花螺,花螺圆滚滚,壳上斑斑点点花纹美丽。那时海里没污染,织纹螺没有毒,十分美味,街边小贩卖煮熟的织纹螺,一分钱一小盅,取一只放嘴里一吸,就可尝到大海的滋味。海泥上还有绿油油的海苔。海苔是春卷的绝配,我却没有捡。海苔需要日晒,晒干后炒熟炒脆才能食用。巴掌大居室,哪有地方晒海苔?涨潮时我也曾去那儿学游泳,独自一人在近岸处扑腾,偶尔不小心呛一口海水,很咸很咸。

晨光里的筼筜湖
1969年我插队务农,1971年初春回厦门的家探亲,那一年四弟16岁,正参加筼筜港建设,我有页日记写到这件事:“和勇弟合一辆板车,我参加了围垦筼筜港的劳动。我很激动,拉车的有许多女青年,有的甚至是小鬼的模样。中国人的吃苦耐劳,足够使整个地球吃惊。到了填海的工地,那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我的眼眶,甚至潮湿起来。何等壮观的场面!两条长堤,像两只巨大的手臂,伸出来,快要握在一起了。堤面有东方红路的宽,堤上无数的广播杆上安着喇叭,喇叭播出的歌声给工地增添无限的战斗气氛。如龙的板车队来往穿梭。精神要高度集中,否则会撞到别人的板车上去。”(1971年1月22日)那一天我就邂逅好友林培堂的胞妹惠玉,她在车流的终点卸土,冲我莞尔一笑,又埋头干活了。后来,她告诉我,她一直干到整个工程结束,号称“铁牛”。那时,厦门千家万户有业的青年每人带薪到筼筜港出工一个月,所有无业青年都义务投入这场移山填海、向海要地的战役中,每人至少一个月。千万青年积极投入筼筜港建设中,每天只领取微薄点心费,其精神可圈可点可赞!我们板车上的土取自金榜山,有一座山头快被削平了,下山的路很陡,载重的板车惯性极大,飞也似的直下厦禾路,板车手跟着飞了起来,只有脚尖瞬间沾地又马上离地。脚步匆匆,汗如雨下,湿透的衣服紧贴肌肉。料峭春寒,却一点也不觉得冷。厦门有许多精神,“海堤精神”“英雄三岛精神”“马塘精神”,等等。我想,也该提倡“筼筜港精神”,那是拼搏精神、奉献精神、为国担忧精神。
当围港的长堤合拢,筼筜港变为筼筜湖。厦门半岛多了一条巨臂与陆地连接,这头沿湖的路叫湖滨南路,那头是湖滨北路。
岛内城区的飞速扩展,可以说是从筼筜湖畔等地方开始。第一次乘车走湖滨南路,到市委常委、部长杨华基家,那片地正大兴土木,路坑坑洼洼,感觉真是条“弹簧路”。当五公里半的湖滨南路及路两旁建筑崭新亮相时,我分明感觉到经济特区茁壮成长,感觉“大道如青天”。我读到《厦门日报》头条:“市地名委员会命名43条新路”,情不自禁写了一首诗《新路》,发表在1985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副刊上:“当楼群象大陆架崛起/亲吻广阔的天空,/在楼海的波谷中/新路一条条诞生!/诞生了色彩斑斓的河流,/诞生了芬芳馥郁的笑声……//我真想把长眠的奶奶唤醒,/扶她走进小‘的士’,/赏一路树苗抽出嫩绿,/看大街橱窗展出画屏。/让女儿坐在我自行车上的藤椅,/乘‘凤凰’逛逛新城,/道路四通八达不断地伸展!//呵,可爱的家乡,/新路可是你强健的神经?/我为你感到骄傲/你以崭新的大道,/召唤新世纪叱咤风云。”
城市快速发展为我们小家庭提供了栖身之地。在这之前,我到杏林电厂探望妻子,她住集体宿舍,我寄宿工厂男宿舍,新婚夫妇,久别相聚,竟连轻轻一吻也成奢望。后来我们住进厦港南溪仔墘那间阴暗潮湿的陋室。1985年7月,单位分配一套房子给我,是湖滨一里67号602室。拿到房钥匙的第二天,我家便搬进还是水泥地板的新居。旧居陋室,没有自来水,用水要到巷口买或到古井挑;没有厨房,有客来访,便用煤油炉煮饭。妻子怀孕时,从杏林风尘仆仆回到厦港家里,我会到大街饮食店买1元的鱿鱼汤,算是给她补身体。相比之下,新居就是天堂,有2平方米的卫生间,3平方米的厨房。第一次在自家浴室里淋浴,痛快淋漓。我请姑父谢重光的胞弟谢澄光写了一幅字“人生从四十岁开始”挂在5平方米的厅里。林培堂看到这幅字,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他写道:“我的挚友陈志铭,是一位热情洋溢的诗人,我和他是同龄人,在我们刚踏进四十岁的门槛时,有一次我到他家,只见大厅壁上镜框里,嵌着一幅谢澄光书赠的‘人生从四十岁开始’的字幅。啧啧,我已觉得‘老去悲秋强自宽’,他犹自壮志踌躇,才要‘开始’事业的奋斗,这真令我自惭形秽。”
新居楼房的地基,建在筼筜港的滩涂上。我颇感慨:我住在大海的胸膛上。夜里酣眠,梦中有一泓深蓝。
1988年3月,市委、市政府机关从公园南路搬到湖滨北路,上班时我常见到一群奶牛走在路上,据说附近有一个奶牛农场。记得我调离宣传部前夕值夜班,把九楼会议室里灯都关了,眺望着尚未被高楼遮挡住的筼筜湖,静静坐着出神。远处灯光,新城区灯光,犹如渔火,甚至比渔火更繁密绚丽。
我在湖滨一里住了十年半,那一段岁月在我人生中有不一样的意义,它贯穿了我女儿小学和中学时光,女儿和父母朝夕生活在一起。小学毕业考,她总成绩在年段里排第六位,学校发给前十名一份奖品:依金钢笔和圆规。那一天她兴冲冲回到家,把喜讯告诉我后,就把钢笔递到我面前:“爸爸,这笔送给你,只是它不是真金的。”女儿13岁生日,我写了一首诗祝贺:“每天早晨/爸爸轻轻一吻/结束了你多彩的梦//从被窝这头钻到那头/咯咯咯咯笑得开心/熊猫式的顽皮/驼鸟式的天真/都令我忍俊不禁/天伦之乐/木床见证/嬉闹滚爬/曾宽绰有盈/而今突然变小/十三个冬春/渺为前尘/十三岁生日/一抹晨曦氤氤/悄悄来临//该以什么祝福/贺你诞辰/孩子,不要只是/在梦中耕耘/为了美梦成真/人生的早晨/不仅仅祝你快乐/还祝你付出艰辛。”
那是一家三口奋斗的岁月,我们少有闲暇到湖边散步游玩。准确地说,到湖边的次数寥寥无几。屈指可数的几次,是为了定格时光的拍照。偎近筼筜湖而和她不亲近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工厂污水和附近居民生活污水都直排湖里,腐臭气味难闻。海水中盐本有腐蚀性,氨气味浓浓的空气腐蚀性很强,家里冰箱、壁灯等物件铜铁部分锈迹斑斑。很长一段时间,我家面湖的窗户都是紧闭的。
家搬离湖滨一里后,我只回去那座楼一两次看望老邻居,当然,也没有闲情逸致到湖边观赏风景。直到最近参加一个培训班,在未来·信息酒店住了几天。酒店就在筼筜湖畔,房间的窗下可见厦门人熟悉的白鹭洲鸽子广场和白鹭女神雕像。几个早晨和夜晚,我多次到筼筜湖畔散步。往中山医院的方向,直走到嘉禾园;往音乐喷泉方向,直走到露天音乐广场。有一首口占《七绝》很说明其时心境:“筼筜湖畔居多载,从未昏晨赏景来。美错重游须酷白,涟漪一片荡心怀。”在音乐喷泉广场前,镶嵌着厦门城市原点雕塑“方圆同心”。厦门城市原点本来在老城区工人文化宫广场,那是厦门明代古城遗址附近,现在移到了筼筜湖白鹭洲公园里,真是日新月异的扩展啊!原点雕塑外圆内方,刻着厦门离北京、上海、西安、福州、香港、澳门、台北和金门的距离,金门理所当然离得最近。宋元明清,金门隶属于同安县,直到民国时期才从同安县分离出去。印象中,筼筜湖滨的苏铁高不过腰,现在已经高过二楼了。漫不经心走着,我想起习近平同志任厦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时主持制订的《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想起他说的话:依法治湖,截污处理,清淤筑岸,搞活水体,美化环境;想起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的话:在全国,“厦门是第一个提到生态问题的”;想起市委、市政府用全市一年基建投入的十分之一,开始了筼筜湖的综合治理;想起厦门发挥河湖长制平台作用,全市333个受污染的小微水体也得到治理,老百姓可以“推窗见绿,出门入景”;想起新华社一篇通讯《从臭水湖到“城市会客厅”——厦门筼筜湖的生态蝶变》。培训班期间我得便去探望八十多岁的彭一万老师,他告诉我,他从家里走到筼筜湖边只需五分钟。我到过几个发达国家旅游,最惊叹的是它们的蓝天白云,行旅匆匆,皮鞋竟不沾纤尘。现在,中国也不乏蓝天白云了,海上花园厦门更是这样。

筼筜湖畔嘉禾园
厦门城市公园很多,在筼筜湖畔,除了白鹭洲公园,还有南湖公园、海湾公园和嘉禾园等。它们各有特色。南湖公园里有“筼筜渔火”“筼筜春晓”“坐石临流”和“曲水荷香”诸景。海湾公园分天园、地园、林园、草园、水花园、滨海风光和星光大道景区。嘉禾园不大但精致,紧挨筼筜湖,美丽拱门后是主雕塑嘉禾神女,体态端庄而婀娜,右手举着一束稻穗,左手向前伸出,臂上衣带飘飘。唐宋时厦门岛被称为“嘉禾屿”“嘉禾里”或“新城”,据说有稻一禾双穗,誉嘉禾。这些公园的共同特点是:园里市花三角梅盛开,市鸟白鹭或亭亭玉立,或翩翩飞翔,花草葳蕤,树冠如盖。美中不足的是市树凤凰木少了点。

海湾公园
筼筜湖由四个湖区组成,水面积共1.6平方公里,虽没有天光万顷,却也是碧波粼粼。因为有了筼筜湖,厦门成了真正意义的城在海上,海在城中。我顺着湖边的栈道和石路走着,清风吹拂脸颊,心中充盈爱意。这一片海域,有我儿时的记忆,有我奋斗的汗水,也收藏我一家三口团圆的温馨。女儿读实验小学时,坐在我自行车藤椅上上学,风雨天我穿雨衣,她就在躲在蓝色雨衣下。那一天大雨瓢泼,我嫌雨衣帽子遮挡视线,骑车不安全,便把帽子脱了。她在一篇作文里这样写道,看到父亲脸上汗水和雨水,深感“爱”为她遮风挡雨,是一片蓝色的天空。女儿中学时代寒暑假,她妈在杏林上班,一日三餐,我是主厨,饱尝人间烟火气。
休闲步道上踽踽而行,记忆的碎片随风扑怀。放眼四周,浓绿欲滴。望湖,湖蓝分五色,有北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霁蓝,有元代玻璃莲花托盏的蔚蓝,还有天蓝、祭蓝、孔雀绿釉蓝。湖里还有一艘淤泥船,厦门人知道,治理和管理这一湖蓝,没有句号。
作为厦门水环境治理先行者,筼筜湖水质净化厂是典范。就在西堤湖滨南路这头,1986年该厂开工建设,这是福建省第一座污水处理厂。此后,该厂一次又一次升级,为筼筜湖重生立汗马功劳。偌大的一片水域,有人提议,可以在湖上搞游船和其他体育娱乐活动或夜游,也曾尝试过,但都始尝辄止,还是让湖享受平静和安宁吧。厦门人民像呵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呵护着筼筜湖。
在西堤湖滨北路那头,建了一个纳潮闸,让湖和海连通,涨潮时纳水进湖,退潮时排水入海。让大海,让鹭江帮助筼筜湖吐故纳新。据有关部门统计,涨潮时纳潮闸可进活水130万立方米,占湖库容360万立方米的36.1%。“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纳潮闸附近,白鹭最多,是拍鸟发烧友的热门打卡地。
我又来到白鹭女神雕像前,常赞叹这世界太多美女充盈魅力,但最美的还是白鹭女神,比安格尔《泉》的裸女更美,她跪在兀立的花岗岩上,正在梳妆,肩头歇着一只白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她全裸而纯真无邪,澄净了观赏者心中的尘埃。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时,曾举办白鹭女神灯光秀,倾城空巷,吸引多少人前来观赏!
现在,无论是岛内还是岛外,厦门在绿树掩映之中,半城绿树半城花。据市园林局统计,厦门绿化覆盖率达45.65%。 这是一颗镶嵌在祖国东海蓝衣襟上的绿宝石。
筼筜湖,是这绿宝石上的一滴蓝。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杂志2025年第2期;作者为原厦门市文化局副巡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十三届厦门市政协特约文史研究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