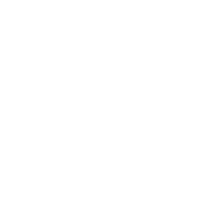那些远去的斑驳背影
——西林怀古
简 梅
很少有一座村落会与唐代一段恢宏、别致的历史结合得如此紧密,在闽越大地上书写传奇。当我觅见它从古至今的延脉传承,并从中窥见其博广深遂的内涵,内心中便一直激荡着释之不去的情怀,并深为之感到骄傲。然而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之后,它的变化,又使人为之叹息……这一切,犹如时而平缓,时而湍急的漳江之水,交汇不已又幽思绵长。这个村落,就是位于漳州市元霄县火田镇的西林古村。
不知为何,抵达它时,雨会下得如此凌烈,天空也黑沉一片,也许在某种契机下还原了这片土地曾经的荒蛮与刀光剑影,以及关山重重、密林狭道的背景下,先人开疆拓土的种种艰难。懵懂的我怀思着:这到底是一座藏有怎样印迹的古城,它为何会牵连世人众多的目光?
脚步从踏上它的那一刻,便一缕缕、一寸寸地勘行。最终,我虽不敢说已全然窥见或掀开了这座漳州故郡经年的风霜,但我仍从它沉淀在时光背后的辉煌里,看到了这里无数先贤以睿智与胆识、勤耕与坚韧铸就的漫漫文明之路。作为故郡,因特殊缘由它前后虽只历经30年,却由此开启了闽南历史的新纪元,中原文化从千山万里外传播至“背山面海”“榛莽如是”的东南边陲,实现了汉越和融,促进了福建农耕文明和经济文化得到开拓性的发展进步。
据《云霄县志》云:“西林城在西林,旧有石城……考其由来,实建自唐高宗年间。”又据《云霄县志·建置沿革》载:“唐垂拱二年,元光请于泉潮间建一州,以抗岭表。朝廷以元光父子入牧兹土,令其兼秩领州,并给告身,即屯所建漳州。故城在梁山脚下,今云霄西林村。”
唐总章二年(669年),一封急电文书惊醒深宫人,泉潮间发生“蛮獠啸乱”,居民苦之。当时的东北边境,唐王朝与高丽交战数年,仍处于重兵屯守紧张时期;西北边境,唐军接连受挫吐蕃军队,良军强将均在外受命,而东南此时又起狂澜……谁能担此重任?唐高宗体弱多病,皇后武则天在身后摄政掌管。身负重任的“归德将军”陈政,因为处事刚毅果断,谋划策略谨慎持重,得以举荐,受诏即率领将校123员,府兵3600名,千里迢迢顺着淮河进入大运河,再沿运河进入浙江,从仙霞岭入闽。沿途马蹄声声,尘土飞扬,绕行了千山万水,之后连克数座强悍的少数民族盘踞的峒寨,抵达今漳平与华安交界的九龙山地界……经过三个月艰难的凭险据守,等来后续接应的唐府兵及军眷5000余名。两军会合,重整旗鼓,击退十八峒联军,进抵九龙山北岸(今龙海角美镇江东桥一带),被汹涌的江水阻隔,只得就地插柳为营,屯兵镇守。他恩威并著,斩荆棘、垦良田、兴村落,安置因战乱流离失所的民众,由此辟建对后世影响意义深远的“唐化里”。休整一阵后,又智取娘仔寨,越过蒲葵关,进屯于火田厚埔一带的故绥安县地,建立起大本营……
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年),陈政带领着年幼的儿子陈元光与年迈的母亲魏敬,在东南边陲艰苦征战8年后,病逝于这块他曾对着漳江之水发出“此水如上党之清漳”的热土。而陈元光从13岁起跟随父亲,临危披阵,少年磨志,肩挑大任,接续父亲未尽事业,开启了“开漳大业”的宏伟之路。
随着陈政及随军的87姓中原唐兵与军眷一路迁徙,我彷佛看到了一条威武不屈又绵长不息的安疆拓彊之途,其间,无论遇到怎样风起潮涌,流离颠沛,总是凝聚着坚固、紧牢的华夏之心。
为了确保闽南一带的长治久安,唐永淳二年(683年),陈元光上呈《请建州县表》,提出“其本则在创州县,其要则在兴庠序”的定国安边方略,因为他明白,如果仅用武力,没有从根本上摘除顽痼,只能让未开化的百姓表面屈服;只有实行礼教,才能匡正他们的内心。他的定边之策,打动了武周的政权,垂拱二年(686年)十二月九日,武则天颁诏《赦陈元光建州县》,批准在泉州与潮州之间的云霄建立漳州治所,管辖漳浦、怀恩二个县,任命陈元光为刺史。父亲当年与他率兵进驻云霄之后,就设三营进行有效的防护,中营的西林以其独特的“东倚梁山而临海,西有大峰山、乌山山脉为障,北有盘陀岭、蒲葵山为护”的地理特征,置于军事力量的保护之下。而且在漳江上游约四五公里处,有一块宽敞的冲积平原地带,因此将它设为漳州治所是较理想的选择。州鉴“漳江”其名,取名“漳州”。
眼看多年的辛苦,使民心有所依归,陈元光欣然抚笔:“三军歌按堵,万骑弛鸣镖”“云霄开岳镇,日月列衙瞻”。将士们与庶民纷纷投入开屯建堡、设立官署等新城的建设中,喜悦之情在翠林、江河中映照、跳跃。之后数年,逐渐形成以西林为中心,呈放射状分布的聚居群,西林也遂成为千家烟火的村集。据明编纂的《漳浦县志》里记载,西林周长3000米,基石三合土结构。城堤宽4米,其上墙厚60厘米,高4米,墙外西护城河,东临江,设四城门。村中至今仍保存着古指挥台、军营山、演兵坛、古水井、将士喂马石槽等遗址和文物,并保留“军营巷”、“粮仓”“盐馆”“五街厝”“总兵寨”“尚书府”等古地名。而陈元光率领将士兴建的拦水坝堰工程,民称“将军陂”,至今还灌溉着千亩良田,成为中原文化在闽南传播的历史见证。
新城落成,陈元光暂时卸下连年的奔劳与激战,全城庆宴。在《漳州新城秋宴》这首诗中,他满怀激情的笔下,浮现出西林古城美丽的景致:“地险行台壮,天清景幕新。鸿飞青嶂杳,鹭点碧波真……东涌沧溟玉,西呈翠巘珍。画船拖素练,朱榭映红云”;《落成会咏》二首中,更是豪气满怀:“泉潮天万里,一镇屹天中……环堂巍岳秀,带砺大江雄”,而“山畚遥猎虎,海舶近通盐”的诗句,也让我们见到当时漳江古码头熙熙攘攘的通商景致。他通过奖掖农耕、通商惠工、任用贤士、兴办学校,和亲通婚,传播中原先进文化与生产技术,改变了“火田畲种无耕读”的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生活方式;并奏立行台于四境,四时躬自巡逻,“由北距泉兴,南渝潮惠,西抵汀赣、东接诸岛屿,方数千里无烽火之惊,号称乐土”。
令人称道的是,他在《示珦》诗中教育他的孩子:“载笔沿儒习,持弓缵祖风……日阅书开士,星言驾劝农。”声声切切都是对这片圣土的热爱与殷切之心,由此深受百姓拥戴。但将军却在景云二年(711年),于出巡途中闻粤东流寇复起,率轻骑讨之,竟身殉岳山……历史终将他推向人神共瞻的悲壮境界。
从这些简约但又力透纸背的点滴史迹中,我终于还原了这个古老村落流淌在它身上的庄严、荣耀而又饱含血泪的历程。
此时,雨越下越大,空气中似弥漫着一种莫名的忧伤,环绕着古村落寂寥的巷道。我来到了西南面的一个颇为雄伟的古建筑面前,村里的老人自豪地告诉我,这就是千余年前陈元光将军治理军机及办公的漳州故郡府衙。这座府衙原来有三开间,有大堂、大埕、仪门,还有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分列的耳室,以及狱司监房、内衙等,占地大约1200平方米。呈现在眼前的古建筑为四方形,墙体为夯土筑就。历经千年的时光侵蚀,房间都已经倒塌,孤零零地伫立着,尽是满目的杂草与残墙,底部经受不住时光与风霜雪雨的侵袭,不同程度剥落,顶部的墙面爬满一些蕨类植物,一砖一瓦无不感叹着历史的变迁。而大门的墙体更是排列着已毁蚀成大小不一的诸多洞孔,穿越了多少尘埃与人间沧桑。瞻望着它们残破的身体,我摩挲着岁月的演变,无情的云烟。
从侧门进入,缀满草叶的厅堂,倒映着早已改变容颜的景物,只有坚实高贵的石条,它们仍铺在厚实的土地下,默默吟唱西林村的变迁:唐,宋,元,明,清……1340多年呀,有多少场的烟雨,炮火,有多少如蚁的人群,从它的视线中来了又去,去了又来。直至今日,它们如入定的禅人,褪尽了一切的喧嚣,与尚存的古屋静默相依。一堵如雕塑般残缺的墙立在眼前,老人们冒雨指点着,这里就是曾经雷厉风行的监房……
穿行于深一脚浅一脚的古老街巷,时而掠过一二个挑着菜篮、戴着斗笠的村民,四周静穆,且有些萧凉,路边不时可见到斑斑的西林旧城墙的基底层砌石痕迹。不久,便到了传说中的演兵坛,坐落于西林城西北,原分三层,由原始土夯筑,周围壕沟环绕;而风雨中我只见到残存的一堵墙约5米高、1米厚,被丛生的杂草包围着,以及依稀可辨的宽厚硕长的土基石墩……面对着满目苍痕,落满积叶的演兵坛,我肃然无言,这里曾经排兵布阵,战马斯斯,盾矛挺立,军纪严明;将军儒姿翩翩,他目光炯炯地遥望着指挥台的正前方百米之外,有一座形似覆锅的山丘,当时的唐军中营就安驻在这个山,现被称为军营山,在城外保护着整个西林城……
我怀着怅惘的心继续参观了尚存的粮仓遗址,厚重精致的石门仿佛诉说着当时粮食进仓出仓的道道严格程序与重兵把守的地位;而北大门的护城河早已消失,被后代填为水田……
雨雾中,四周缥缈,当我转到古渡码头时,见到漳江水依旧缓缓流淌,两岸自由生长的林木宠辱不惊,带着自由的姿态,仿佛对我说:不惊!不惊!生命的历程从来都是如此。溪边停靠着一二只简易的木筏,有两个淳朴的大姐靠在岸边洗衣服,溪水倒映着她们勤劳的身姿,而衣物飘拂在溪中,晃动着安逸、与世无争。码头的对面即著名的五通庙,据《平和县志》《云霄县厅志》记载:“查此庙石栓镌有盘、蓝、雷字样”,可谓“云霄宫庙唯此最古”。庙中祀着汉将周亚夫,即广平尊王,传为陈政、陈元光父子南征时从中原包“香火”分灵于此,为开漳将士保驾护航;元朝时陈君用修城时增祀“五方之神”五显帝于此,谓称“五通庙”。一株千年古榕守护庙前,彷佛依旧迎迓着将军归来……
《春秋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村中遗存重修的上林圣宫,庙柱上印刻着一副著名的对联“唐史无人修列传,漳江有庙祀将军”。是啊,在长达150年的时间里,自陈政为开漳先驱以来,经其子陈元光为之奠定基业,继由其孙珦、曾孙酆、玄孙谟蝉联刺史。五代相继,领袖一州,率众启土,遗爱万民。可惜新旧唐史均略而无传,以致元人张翥曾发出“功名不到凌烟阁,读尽丰碑泪欲流”的悲叹。这应该与当时唐王朝关于“正朔”的宫廷讳忌有关,陈政、陈元光等开漳圣土的功勋卓著,却与“无字碑”这段历史有着惊人的吻合,无论是有意或无意抹去史迹,却幸凭百姓的口碑得以永垂后世。
“西林村大都姓张,这个张姓就是唐朝府兵87姓中的一大姓。”采访中的西林村张主任与另二位陪同的老人都姓张。岁月更迭,后来,府兵们的后裔移居台湾、东南亚以及欧美各地,均以“唐人”自称,并把当时的大唐江山称为“唐山”。由此“唐山”成了海外侨胞对祖国或故乡的一种习惯称呼。
时光渐渐剥离过去斑驳的光影,“开漳圣王”的精神,却一代接着一代,延续着中华寻根、正义、仁爱之梦;西林村的故事也一个接着一个,抒发着对开漳先贤们无比崇敬的心思。
(本文原载于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省作协“走进八闽”文化采风系列之《走进云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