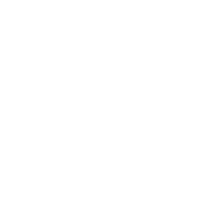我家在“8·17”前后
刘含怀
赶回福州迎解放
1949年炎夏,中国人民解放军挥戈南下,由浙、赣两省分路入闽,势如破竹,福州解放指日可待。当时我在厦门大学毕业班读书,不但可从与地下党有联系的同学那里获知解放福建的大体进程,就是从国民党《中央日报》所谓的国军不断“战略转移”的战报中,也可以窥测到蒋军节节败退的真相。于是,我们30多名福州籍的毕业班同学,要求校方提前考完最后几门课程,抢在福厦交通尚未中断之前赶回福州,迎接解放。
我是1947年秋天从新加坡回国到厦大续学的归侨。我的护照(新加坡入境证)是5年期;堂兄刘强博士是新加坡教育界名流,已为我在新加坡一所中学谋取到教员职位,叫我一毕业就出国应聘,我去信婉辞。堂兄觉得很奇怪,再次来信劝促,要我当机立断,不要在十字路口徘徊。其实,当时我面前并不存在十字路口,我已作了“留下来”的最后抉择。这固然是有老母在堂,再不让我远行,而且我结婚两年的妻子即将分娩,有家室之累;很主要的是我和父亲(也是归侨,也有未过期的出国护照)都有了“参加革命,投身新中国建设”的打算。父亲大学毕业,威严、自信又很通达明智,先是从教、从政,而后去南洋从商,20世纪30年代是拥有巨资的经营木材和闽江内河航运的民族资本家。但他在南洋是个深受陈嘉庚言行影响的爱国者,福州解放前夕,他毅然决然从台湾搭乘最后的班机赶回福州。福州解放后他又真心诚意地代表资方,按党的赎买政策,与政府合作,把福建闽江轮船公司这一福州最大的运输企业交还人民。他也因此得到政府与人民的信任,连选连任了两届闽清县人民代表和福州市华侨特邀代表,成了爱国民主人士。经政府批准,他于1953年再度出国,到马来西亚沙捞越受聘主编“中间偏左”的民办报纸《诗华日报》。他对新中国的建设和华侨政策作了正确的报道和宣传,同时用巧妙的文字措辞纠正或辩驳了“偏右”及反动报纸的歪曲和诬蔑。一直到1964年七旬之年落叶归根,回到福州老寓养疴。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个父亲高兴。
箪食壶浆迎义师
我和父亲先后从厦门和台湾回到福州家中时,福州守敌在解放大军包围下已成瓮中之鳖。我家住仓前山跑马场旁边,国民党军队溃逃前,汤恩伯还在跑马场作了一次阅兵,我家门口一路上布满了荷枪实弹的蒋兵,禁止居民自由出入。临解放了,我们全家人的心情是既紧张又兴奋又害怕,担心蒋军逃跑前炸城、抢劫、杀人。我、父母、妻子,还有个念初中的小妹成天都待在故居“乐天山馆”的楼屋里。三楼有几个窗口朝着马路,跑马场也在我们的视野里。8月17日上午,国民党军顽踞在万寿桥南侧的最后桥头堡被英勇的解放军摧毁后,就仓皇向福厦路方向溃窜,其中有一股退到跑马场,沿着场边的田埂向义序机场方向遁逃。我家大门和窗户紧闭,只敢透过百叶窗窥视一群群嘈杂混乱的蒋兵狼狈地从屋边跑过,前后约莫有数百人。半晌,一队扛着步枪机枪的队伍赶上来了,有的手臂还扎着红布条,我一眼瞧见就不由自主地惊呼:“快来看,十兵团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不进民房,露宿福州街头(肖海摄)解放军来了!”赶紧把百叶窗打开,全家都趴在窗棂上,看着跑马场上解放军架起迫击炮,“咣咣”地向义序方向发射。父亲沉着心细,一清早就吩咐母亲和老女佣烧了一大桶开水,还盛了一小桶昨夜磨好的豆浆,大声发话:“开大门,挑开水、豆浆慰劳解放军去,这叫‘箪食壶浆迎义师’嘛!”他捻了捻唇边的二撇须,神情兴奋得很。许多邻里也都陆续开门出来了,送茶送水的远不止我们一家。解放军只舀开水解渴,茶和豆浆、馒头什么的一概婉谢不沾。傍晚停止行军时,解放军官兵都坐着或躺在马路两旁屋边歇息、过夜,怎么请他们进屋都不依,不折不扣地秋毫无犯。

十兵团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不进民房,露宿福州街头(肖海摄)
家有闺女名“解儿”
也就在迎解放的那些日子,有件事令我非常焦急,因为我妻子的预产期就在8月中旬。8月15日那天我陪她去塔亭医院妇产科检查,在麦园顶高处已能隐约听到从北门方向传来的枪炮声。我半开玩笑地对她说:“福州解放就在这几天了,你就再忍一下,把孩子产在解放区吧。”果然,天从人愿,她超过了预产期,于福州解放后的第7天,她在充满阳光的塔亭产房里顺利地生下了我的第一个女儿。
福州解放后不几天,《福建日报》就出版了。我们都从这份崭新的人民报纸上学习了解眼前的新战况、新政策、新生活。“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很快就成为福州市最流行的歌曲。我相信“解放”将给我家带来光明的未来。我想起女儿快满月了,该给她取个名字;还想起,自己既然留下了,就得赶快找到工作,参加革命;还想到,父亲对自己的下半辈子又有什么打算呢?我找父亲谈话。父亲慈祥地对我说:“过两天你女儿就要满月了,我要办一两桌酒为小孙女做满月。”我问小孩该取什么名字。“到时再说吧。”他狡黠地对我一笑,看来他早已心中有数了。
9月25日女儿满月家宴上,父亲兴致勃勃地叫我妻子把婴孩抱到席前,当着亲友们的面,喜滋滋地宣布:“这个女孩是我刘家的第三代,我给她取个好名字,叫刘解儿。这名字有两层意思:一是迎接解放,二是女儿就是儿,通俗点讲就是解放的儿子。”全席欢然,纷纷举杯向我父母,向我们夫妻祝贺。我真没想到,在国民党旧社会活了半辈子的父亲,脑子竟然如此“飞跃”!
交上“自传”干工作
现在该轮到我解决“参加革命”的问题了。当时福州是军管时期,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除南下干部外,只录用一部分愿意参加工作的国民党留下的旧人员,没有大量向社会招收人才,对应届大学毕业生还没有“统一分配使用”这个制度。所以我只好“毛遂自荐”。我在厦大念的是经济系,希望能“对口”投身人民银行。当时省银行由福州军管会金融处管辖,行长由金融处主任方毅兼任,副行长是高磐九。我写封情真意切的求职信并附去一份自传。如果是一个纯粹的刚毕业的大学生,其自传是没有什么跌宕曲折的情节的,但我是近30岁的大学“老”生,已经历了一些人世沧桑。我在1941年夏读完厦大二年级后曾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流浪了几年,在自传中我真实而又激情满怀地描述了我中学和大学时代读过和写过的倾向进步的文艺作品,曾被视为“思想激进”在连城被国民党抓捕过;“二战”期间,到了新加坡,又因参加抗日活动在日本法西斯监狱蹲了两年的牢,释放后逃往北马抗日军游击区,接触了一些马共成员。坐牢、失业、挨饿、当小贩、当教员、当记者,有过受磨炼的丰富经历,或者更主要的是我在自传中流露出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新中国的憧憬和对参加革命的强烈要求,因而打动了审阅者的心。我于9月28日托人把报告交上去,10月10日就被通知去省行人事科谈话。
我一进房内,就瞥见我的自传摆在林弛科长的桌上,上面有一行大字批语:“这是个大学生,我看还可以。高磐九。10月7日。”在高副行长“还可以”的批语下,我次日就正式上班了,而且“正对口”地把我安排在调研室当一名金融业务刊物的编辑。
这是福州解放一个半月后的事了。不久银行需要两名译电员,我就向人事科林科长推荐我妻子,说她具备译电和打字的技能。经过考核面试,她也被录用了。在那段时期,台湾国民党方面蠢蠢欲动,银行和各机关白天“躲空袭”,晚上上班。妻子搞译电,要等银行业务都结束后她的电报才能译发,所以每晚都要拖到深夜十一二点。我在营业厅走廊等她下班,然后用自行车载着她翻过吉祥山的斜坡,跨过英雄的解放大桥回仓前山的家。我们一路迎着暮秋冷飕飕的凉风,披着满天闪烁的星光,哼着当时流行的“打得好来打得好”的歌儿,有时还会突然想起一个月前共和国诞生的那一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发出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响彻世界的宣言,深为自己能做为新中国的主人而感到自豪和幸福。
(作者系福州市著名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