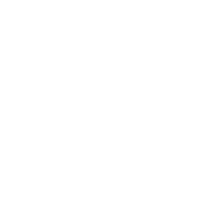20世纪90年代,我所经历的石狮宣传工作
陆开锦
1991年10月到1993年10月,我被省委选派到石狮市挂职锻炼,任市委常委,协助时任市委副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的黄源水同志分管宣传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那两年,既是石狮历史上最火爆的一个时期,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历练。现在回忆起来,有许多值得怀念的地方。下面,我重点回顾与宣传工作有关的一些情况。
就挂职干部这项工作而言,我们算是省委选派的第一批。对此省委非常重视,专门在省计委培训中心举办培训班,请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为我们讲“青年干部的成长”,时任柘荣县委书记的钟安同志讲“如何当县委书记”,时任顺昌县县长的梁模同志讲“如何当县长”,时任省组综合处处长的李川同志讲“如何当处长”。从年龄来讲,我是第一批挂职干部中最小的一个。我非常珍惜这次锻炼的机会,因为这是我离开高校、机关后第一次真正地深入基层、深入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省组本来是安排我去漳州芗城区委,后来是省委办公厅出面沟通,改派我去了石狮市。这里面有个背景。1991年3月,省顾委8个老同志由黄扆禹同志带队,到石狮进行为期13天的调研考察,给省委上报了一份关于石狮市“两个文明”建设情况的报告;5月23日,陈光毅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专题听取了省顾委的报告。报告在肯定石狮建市以来取得的成绩和主要经验的同时,也提出石狮“两个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特别点到众多的侨商、外商为石狮带来观念、技术和信息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次省委常委会会议对石狮工作提出了四点意见,最后一点是“对石狮市发展中的经验、问题,有关部门要帮助总结,省委政研室要经常去调查研究,省委宣传部可以组织理论界的同志去研讨,以帮助和推动石狮市的工作”。根据这次会议精神,省委办公厅认为派我去石狮工作,既可以得到更多的锻炼,又可以协助完成省委交给的课题调研任务。就这样,我来到了石狮,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基层历练。
石狮原本是隶属于晋江县的一个沿海乡镇,由于严重缺水、土地贫瘠,移居海外的乡亲众多,成为著名侨乡,历来市场活跃,与海外联系紧密。改革开放后,石狮的侨乡优势得到了发挥,从香港进来的服装、电器等小洋货,充塞了大街小巷。本地群众也利用侨乡所特有的资金、房屋和劳动力,办起了家庭工厂。一时间,石狮成了全国最重要的、知名度最高的服装小商品市场。有人形容当时石狮的盛况:“铺天盖地万式装,有街无处不经商。客来四海皆惊异,货去神州尽道洋”。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也随着商品和人潮涌入泛滥开来,尤其是走私和黄色现象屡禁不止,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县虽然多次派出工作组到石狮进行专项整治,但收效甚微。关键是体制的问题,作为镇级行政建制,缺乏相应的机构和足够的力量,无法满足石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在各方共同努力下,1987年12月17日,国务院批准,以石狮镇为中心,连同邻近的蚶江、永宁、祥芝3个乡镇,合并成立县级石狮市。经过近一年的筹备,1988年9月30日,石狮市政府正式挂牌办公。从这一天开始,在中国的东南海滨,一座新兴的城市诞生了。
我到石狮工作时,石狮刚建市3年,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小政府、大社会”的体制改革,更是在全国独树一帜。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石狮的活力更是如火山爆发,面积只有24平方公里的小小镇区,每天进出的车辆近千部,客商近5万人,可谓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昼夜不息、财源滚滚。它的个性如此突出,内涵如此丰富,知名度一度超过了它的“顶头上司”泉州市和“母体”晋江县。“不到石狮,等于没到福建”是当时的一种流行说法。石狮成为名闻遐迩的“综合改革试验区”,被誉为“中国民办特区”。
独特的历史和发展背景,为我的挂职经历,同时也为石狮的宣传工作涂上了鲜明的时代底色。
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为石狮市场经济发展和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思想和舆论环境,同时要扩大石狮的知名度,树立正面的形象,改变人们对石狮的负面看法,这是当时石狮宣传工作的重要出发点和着力点。为此,我们组织了一系列重要的宣传活动。一是依托市委办创办了《石狮研究》刊物,发动市领导和机关干部结合本职工作,总结石狮发展的经验,探讨石狮改革开放之路。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每个市领导和主要部门的领导都在该刊物发表了文章,成为石狮机关干部学习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讨石狮发展的重要园地。在此基础上,与刘成业一起,汇编出版了《石狮试验——我们的思考与实践》一书。二是为扩大石狮在海内外的影响力,在《福建日报》开设了“石狮经验谈”专栏,在《香港商报》开辟了每月一期的专版。1992年底,我和市委办的胡毅雄合作撰写了《醒狮腾跃又一年》,占用了《香港商报》的一整个版面。三是邀请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张胜友,到石狮撰写解说词,拍摄了《石狮之谜》和《石狮启示录》两部政论片,在中央电视台四套播出,并通过卫星电视向全世界播送,引起很大反响。四是参与创办现在《石狮日报》的前身《石狮信息报》,招聘祖籍莆田、时任《宁夏日报》总编助理的余光仁及我的中学同班同学、当时在《闽东报》工作的陈永章参与办报工作。五是多次给市直机关干部上党课,还被省委办公厅、省直机关工委及驻军部队请去做报告,向前来参观学习的领导和客人介绍石狮市场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情况。由于理论与现实结合得比较好,每次讲座、报告都取得较好效果。
与此同时,我发挥自己的优势,撰写发表了一批宣传石狮的文章(有的是和胡毅雄等同志合作的)。比较重要的有:《论石狮姓“社”不姓“资”》《历史文化背景和石狮人的性格》《石狮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与启示》《石狮民营经济探讨》《企业家资源和石狮发展》(此文被上海的《报刊文摘》摘转)《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迈向现代化文明》等,分别发表在不同的报纸、刊物上。1993年底我回省委政研室后,又协助王镇辉主任、蔡德奇副主任撰写出版了《石狮:大变迁与新趋势》一书,请著名经济学家林子力作序,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上这些文章,是我文字工作生涯中分量比较重的一批文章。现在回头来看,不少观点至今还是站得住脚的,一些观点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这些文章,后来大部分收入蔡友谋主编的《海内外石狮人著述资料汇编之陆开锦卷》。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论石狮姓“社”不姓“资”》这一篇。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结构,石狮公有制经济比重小,经济运行以市场调节为主,少数人财富积累迅速,加上比较严重的黄赌毒等丑恶现象,一直以来,存在着石狮是姓“社”还是姓“资”的议论。改革开放以前,石狮就有“小香港”“小台湾”的说法;改革开放后,又有“福建的‘一国两制’”之称;建市后,由于实行“小政府、大社会”体制,又有人认为“小政府是共产党的、大社会是资本主义的”,等等。对于这些看法,石狮的领导干部虽然很不服气,但在认识上也不清楚,说起这个问题总是不敢理直气壮,而往往采取回避方式。这给他们的思想带来了巨大压力,成为影响石狮发展的最重要的思想障碍。我在这篇文章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认识社会主义,从石狮的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来理解其发展的道路,得出石狮是社会主义的石狮,而不是像一些人认为的是走资本主义的典型。这篇文章先是在《石狮研究》上刊发并作为市委文件下发,而后又在《理论学习月刊》发表,被评为“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理论征文”二等奖。
这篇文章体现了我的理论功力,对我在石狮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助力作用,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的一个老教授看了后,给予较高评价,专门到石狮来调研,指名要见这篇文章的作者。当我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见我这么年轻,有点不太相信是我写的,后来经过深入的交流,得知我是北大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的,才相信此文确实是出自我的手笔。
还有一次是去海防13师讲课的事。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全党上下都在学习,海防13师举办了一个团级以上干部专题培训班,邀请石狮市委书记去讲课。书记没空,推荐我去。13师派了一部车一个干事来接我,到了师部,师长、政委看到我这么年轻,脸上显露出了不高兴的神情,大概是不大相信这课我也能讲好。当时我刚好写了《论石狮姓“社”不姓“资”》一文,于是我结合石狮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谈了我的学习体会。由于理论与实际结合得比较好,讲座取得良好的效果,得到了全体学员的点赞。后来师政委专门到市委拜访书记,感谢市委派我去做了一场很好的报告。
在石狮工作期间,由于分管的工作关系,也因为和兴趣爱好有关,我与当地文化艺术界的来往比较密切。当时外地人对石狮有一种说法,说石狮是“商品经济的海洋,文化精神的沙漠”。这当然是对石狮的一种不正确的认识。外人初到石狮,眼见的是铺天盖地、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而对其隐藏并渗透到物质背后的精神文化的东西,自然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洞见的。上海一家报纸的一篇文章竟然说:“石狮只有凤里庵门前的那只石狮子是干净的”,还有一位著名作家写了篇关于石狮的文章,标题就叫《欲望的温床》。但当我深入探寻石狮的历史之后,了解到更多的石狮人的故事之后,我才发现,石狮真是一个不简单的地方,是一个真正藏龙卧虎的地方,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其独特的城市精神,足以让很多地级市望尘莫及。
举个简单的例子,为了改变人们对石狮的看法,民间藏书家蔡友谋于1992年发起成立了“绿洲读书社”,不仅组织大家读书,定期出版供大家学习交流的刊物《书馨》,而且编辑出版《海内外石狮人著述资料汇编》系列,至今已出版30种,计划出版50种。在一个县级小市,能够为这么多人出版专集,在全国应该也是少见的吧。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石狮是一个文化的宝库。
说到与石狮文人的交往,真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记得当时活跃在石狮文坛上的,除了藏书家蔡友谋外,还有写小说的陈惠国、邱婷婷,写散文的黄明定、高寒,写诗的蔡白萍、马建荣,写对联的胡毅雄、蔡长泰,还有搞书法的郑伯洋,玩摄影的蔡宏义,研究石狮历史的李国宏以及祖籍石狮、人在香港的著名诗人与散文家蔡丽双女士。我与这些作者常有来往,也经常参加他们举办的各种文学活动。当时,福建文学杂志社的郭碧良正在石狮采写石狮大报告,后以《石狮·中国民办特区》为名出版;省宣的杨国栋、郑振泰、王晓岳正在写长篇报告文学《东方醒狮》;作家庄东贤在石狮挂职市长助理,后来以石狮为背景,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乐城纪事》;《福建文学》杂志主编黄文山、副主编施晓宇等常来石狮举办文学讲座。可以说,当时的石狮文坛,是一片繁荣热闹的景象。
我与他们的交往和结下的情谊,是我对石狮最美好的回忆。离开石狮后,我与他们仍保持一定的联系,有几次还回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当蔡友谋寄来《清华水木——吴清水回忆录》,蔡白萍寄来散文集《另一种完美》,高寒寄来《情字一身债》,吴彦南寄来《吴彦南论述文集》,胡毅雄寄来《一个家族的百年兴学史》时,我都欣然为他们写了序言或是评论。
我认为,在石狮人身上体现了一种特有的精神。2004年,首届闽商大会召开前夕,我在为省委主要领导起草讲话稿时,概括提炼出32字的闽商精神:“善观时变、顺势有为,敢冒风险、爱拼会赢,合群团结、豪侠仗义,恋祖爱乡、回馈桑梓”(其中“合群”两字,是请教了汪毅夫副省长,他提出的)。当时在思考如何概括闽商精神时,我脑海中立即浮现出了石狮人(包括晋江人)的身影,我觉得他们是闽商的代表。闽商精神体现了福建海洋文化的特质,其内核是爱国爱乡、敢拼会赢。这种特质的形成,与石狮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社会结构等诸多因素有关,是石狮人面对生存困境时的一种自主选择。在《历史文化背景与石狮人的性格》一文中,我从海港经济、私商传统、侨乡社会、家族制度等历史变迁的角度进行回溯与探讨,提出石狮人具有独立自强的个性、敢于冒险的精神、正视现实的态度、输人不输阵的肝胆义气、勤劳讲效率的民风、精于算计的商人意识。正是在具有独特性格的石狮人群体中,成长起了一大批敢为人先、善于经营的企业家队伍,成为中国最有实力和竞争力的商帮之一。在为吴清水回忆录作序时,我用了这样一个标题《一个人的历史和一座城市的精神》。2018年8月21日,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从姑嫂塔到镇海楼:一种精神的力量》,我在文中提到了蔡友谋、许荣茂、蔡世佳等石狮人,论述的主要也是他们身上所体现的特有的精神。
现在,改革开放40多年了,我离开石狮也30年了,无论是我们国家,还是石狮市,历史又何止翻过了一页!今日的石狮,与我在的时候相比,早已鸟枪换炮、不可同日而语了。30年前的一些事,现在看来,有的已经陌生,有的变得不可思议了。比如,关于石狮到底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这在当年是一个很重大、很现实、急需回答的问题,可在今天谁也不会提出类似的问题了。如果说30年前的石狮,有点像初生的牛犊,天不怕地不怕地往前冲;现在的石狮,则已经长大了,少了份鲁莽,多了份成熟,更加稳重大气了。有人说,石狮的个性已失,知名度也没那么高了。而我认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它表明了我们国家的整体进步。石狮只是一个县级市,不应该、也不可能让它长期地承担超出一个县级市的责任。从石狮的发展变化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变化,看到未来中国的某种走向。可贵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石狮所具有的内在基因,依旧保存了下来,仍然在支撑着它的发展。石狮,仍具有某种标本的意义。我相信并祝福石狮,在新时代的大潮中,必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系福建省文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