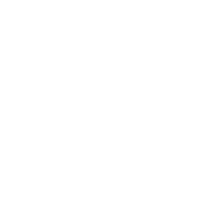侯官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
薛 菁
侯官文化是在福建的自然地理与社会历史背景下,在宋明以来闽学的浸润与观照下,以及清朝末季这一地区中西文化激荡交流中,形成的一支具有福建标识意义的地域文化。其既是福建土著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不断融合的产物,又是与西方文化不断交流、创新的结果。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侯官文化是西方文化中国化的产物,其所具有的爱国自强、开放包容、敦厚务实的精神特质,在中国近代史乃至中华民族复兴史上占居重要地位,与中国式现代化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所谓“现代化”,是指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变迁过程,是在社会分化的基础上,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先导,以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为主要内容,表现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协调发展的社会变迁过程。历史地看,欧美国家率先开启现代化进程,即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迁。过去的五百年,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发展的认知中,现代化就等于西方化。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又说:“它(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也说:“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这种说法已经成为世界的通论,不仅西洋各国人民自诩为文明,就是那些半开化和野蛮的人民也不以这种说法为侮辱……于是有的就想效仿西洋,有的就想发奋图强以与并驾齐驱。亚洲各国有识之士的终身事业似乎只在于此。”[2]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西方式现代化是植根于西方文明——一个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综合体。在这一综合体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文明论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两大传统。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为明证。惟其如此,有学者将西方式现代化称为“西方侵略式现代化”,并在当前社会历史条件下受到了来自实践和价值等诸多方面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植根于中华文明、立足于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提出,彻底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和西方现代化理论一家独霸的局面,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选择。其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近代以来,面对前所未有的劫难,英雄的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一次次抗争、一次次求索,历经百余年浴血奋战,取得了民族独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仅仅用七十余年就让超过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全部摆脱贫困,坚持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的现代化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近代福州的知识精英发挥了重要作用。
鸦片战争后,福州作为“五口通商”之一,成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涌现出以侯官人林则徐、严复、陈季同等为代表的翻译家群体,他们在中国传统经世致用的原则下,自觉研究西方、学习西方,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们的译作为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早在1839年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时,为探访夷情,遣人广泛搜集广州、澳门外国人出版的各种报刊,物色聘用翻译人才,设立译馆,翻译各类书报,组织幕僚翻译英人慕瑞所著的
《世界地理大全》,并亲自润色,编成《四洲志》,成为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地记载了亚洲、非洲、欧洲、美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志书,被梁启超称为“新地志之嚆矢”,[3]也是魏源编著《海国图志》的基石。正是在《海国图志》这部著作中,魏源继承发展了林则徐“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思想主张,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成为那个时代之空谷足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是经世派代表人物在鸦片战争以后面对西学传入所作出的理性选择,是中国应对西方殖民者入侵的主要手段,也表明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思潮一开始就和爱国精神交融在一起;而且它是对19
世纪40年代前后中国社会出现的趋新思想潮流的高度概括,是对“经世致用”文化传统的丰富和发展,[4]为后继者开拓了一个向西方学习的新方向,是近代中国重要社会思潮——“中体西用”文化观之先导,倡日后洋务运动之先声,对后来维新思想的产生亦具启发意义,成为传统经世之学向近代新学转化的发端。嗣后,无论是洋务自强运动,还是维新变法、民主共和甚于科学与民主思想都是“师夷长技”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
林则徐的翻译活动改变了明末以来西语翻译以外国传教士为主导的局面,开启了国人从本国的实际需要出发,自觉、自主译介西方新知识的时代,引发了“西学”热潮。殆及清末,翻译西书蔚为风气,翻译领域迅速扩大,除宗教、自然科学外,还有社会学、文学等方面的著作。如《清史稿》所云:“清之末叶,欧风东渐,科学日昌。同治初,设江南制造局,始译西籍。光绪末,复设译书局,流风所被,译书竞出,忧世俊英,群研时务。”[5]美国华裔学者张馨保如此评价林则徐:“在所有19世纪的中国政治家中,林则徐的形象和影响都超过了其他人。……比曾国藩、李鸿章早二三代人的时间,林则徐就已提倡和发动了向蛮夷学习的自强运动”。[6]林则徐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倡西学之始,开新学之路”第一人。
严复是近代中国“西学第一人”,“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是近代中国系统引进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第一人。从1895年至1908年间,严复翻译出版或发表的西学名著主要有《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穆勒名学》《名学浅说》,内容涉及哲学、经济学、法学、逻辑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诸领域,约200万字,后人称为“严译八大名著”,或“严译八经”。尤其是1898年《天演论》的出版,震动全国,“风行海内”,名噪一时,给当时处在学问饥荒环境中的思想界输送了新鲜的食粮,给正在进行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全新的世界观,从根本上打开了国人的眼界,使得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深入人心,几乎成为20世纪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奋起谋求救国图强的醒世箴言。严复成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
严复通过译述西方近代的学术文化经典,介绍和宣传传西方新兴的资本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自己改造中国传统社会、亦即中国传统社会现代化转型理想与主张。他“所选译的书都是他精心研究过的”,“他均能了悉该书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关系,和与中国古代学者思想的异同”。[7]
立足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维、以儒家传统中的基本价值理念为基点来介绍和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努力寻求中西思想的一致性,是严译著作的最大特色。他模仿先秦文体,选择“汉以前的字法句法”,力图通过用最典雅的中文表达西方思想来影响讲究文体的文人学士。在翻译中,他或常常加入大量的“按语”以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有的按语之长,超过译文;或结合中国时局对原文进行损益、改造,以使西方社会整套的富强之学在中国社会中植根,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严复的译著堪称西学中国化的典范。他借助西方先进理论,通过译著西方学术思想和政治学说以警世,诚如他自己所言:“意欲本之格致新理,溯源竟委,发明富强之事,造端于民。”[8]他“代表了近代中国向西方资本主义寻找真理所走到的一个有关‘世界观’的崭新阶段,他带给中国人以一种新的世界观,起了空前的广泛影响和长远作用,这种启蒙影响和作用不只是在戊戌时期和对改良派,更主要的更突出的是对后几代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年轻的爱国者”。[9]

严复
在严复学术思想中,西方现代学术与中国古代经典是其两大基石。中学是严复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他认为中学“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陶炼”,学习西学的目的旨在“归求反观”中学。对待西方文化,严复强调要“择其所善者而存之”,甚至认为“新学愈进,则旧学愈昌明,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为此,他试图在二者建立一个全面的、理性的、平衡的互动关系:“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10]由此充分体现了严复对外来文化的开放包容,也彰显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更体现了他对建构中国近代新型的文化体系的良苦用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严复重新审视西方文明,尖锐指出:“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11]又说:“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宇。”[12]他甚至写道:“往闻吾国腐儒议论谓:‘孔子之道必有大行人类之时。’心窃以为妄语,乃今听欧美通人议论,渐复同此,彼中研究中土文化之学者,亦日益加众,学会书楼不一而足,其宝贵中国美术者,蚁聚蜂屯,价值千百往时,即此可知天下潮流之所趋矣。”[13]显然,在中西方文化的取舍之中,严复开始从追慕西方转向了弘扬传统,开始抛弃西方文明转而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救国之道,回归本土的精神价值,进而认为中国儒家文明代表了“天下潮流之所趋”。从此,我们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开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探索——这就是寻求一个既高于传统文化,又高于西方近代文明的更高级的文化模式,一个既体现现代化道路的一般规律又契合本国具体实际的、代表人类社会进化方向的新型模式。对这一模式的探求乃是严复之后几代知识分子努力的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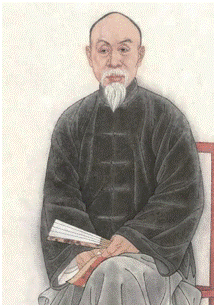
林纾
时与严复并称的闽县人林纾,是我国翻译文学的奠基人。林纾从1899年发表第一篇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至1924年逝世的25年中,翻译的西洋小说“百数十种”,译著之丰为中国近代译界罕见,号称“译界之王”,与严复并称译界“双子星”。
林纾翻译的作品源自英、法、美、俄等十几个国家,其中不乏世界公认的文学名著,如托尔斯泰的《复活》(林译《心狱》)、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林译《块肉余生述》)、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林译《魔侠传》)、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斯陀夫人的《黑人吁天录》、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等等,不一而足。其所译小说在清末民初影响之大,被冠以“林译小说”之称,成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西洋文学经典的代名词。中国读者从林译小说中了解到西方的社会风貌、文学流派、文学大师,打开了中国从事文学者通往世界文学的窗口。林译小说旨在“冀吾同胞警醒”,成为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组成部分,对之后的新文学运动有深刻影响。五四时代的作家们,如周作人、郭沫若、冰心、郑振铎等,早年都有过一个耽读“林译小说”的时期。著名文学家郑振铎在1924年11月11日《小说月报》发表《林琴南先生》一文评价道:“他以一个‘古文家’动手去译欧洲的小说,且称他们的小说家可以与太史公比肩,这确是很勇敢的很大胆的举动。自他以后,中国文人,才有以小说家自命的;自他以后才开始了翻译世界的文学作品的风气。中国近二十年译作小说者之多,差不多可以说大都是受林先生的感化与影响的。”[14]文学史家阿英曾说:“他使中国知识阶级接近了外国文学,从而认识了不少的第一流的作家,使他们从外国文学里学习,以促进本国文学的发展。”[15]
如果说,严、林以译西书名世,那么,陈季同则以传汉学著称。陈季同一生经历过各种重大的历史事件,然其影响最大、成就最著者当是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他是中国近代中学西传第一人,是将中国传统文化译介到欧洲的第一人,与辜鸿铭、林语堂三人并称“福建三杰”。其在欧洲的15年间(1877-1891),正值西强我弱之时,当时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是落后甚至野蛮的,乃至于“几乎没有一个欧洲(包括德国)思想家认为中国社会及文化有可取之处”。[16]陈季同意识到这是闭关锁国的恶果,认为“错误的形成来源于偏见”。为了消解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让西方人更好地认识中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及其价值,陈季同从1884年开始,一直到归国后,始终笔耕不辍,用流畅的法文写了大量著作,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并在作品中向西方读者建构了一个美好而理想的中国形象。可以说,在清末的文人中,没有人比陈季同在西方更引人注目。巴斯蒂赞扬陈季同是“巴黎文艺沙龙受欢迎的人,他用法语把许多富有魅力的中国民间风俗和文学作品介绍给法国人。这些作品后来由新闻记者富科·德·戴蒙翁编辑出版”。“在他的身上,显示出那些最早直接深入欧洲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国人所创造的成果中最奇妙的混合物。”[17]其当时在法国畅销的著作主要有:《中国人自画像》《中国戏剧》《中国故事集》《中国人的快乐》《黄人的小说》《黄衣人戏剧》《中国人笔下的巴黎》《吾国》等,在巴黎文学界颇有声誉,“西国文学之士无不所服”。他翻译的《聊斋志异》,题为《中国故事》(《中国童话》),是该古典名著最早的法文译本,也是中国人自己翻译该著的最初尝试,法国著名作家法朗士为之写书评,称此书“比以前的所有同类翻译都要忠实得多”。还有,《中国人的快乐》一书中多处提及陈季同家乡福州的习俗,如:泰山神的游行、福州的温泉以及清代福州地方文人盛行的折枝诗会。陈季同对折枝诗(又称“诗钟”)的缘起及其在福州盛行的情况作了详尽描述,还例举了许多诗赛上的佳作加以说明,这不能不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学者钱林森对于陈季同有极为深刻的评价,他说:“作为中国文化和文学的阐释者,作为中西交通最初的沟通者,陈季同的创造最具价值的部分,不是他直面西方文化时所流露的自豪甚至自夸的情愫,而是他正视西方文化时所拥有的比较意识(如《中国人的戏剧》)、自省意识(如《巴黎人》),以及在移译、阐述、运用中国文学和文化时所表现的现代意识、创造意识和世界眼光(如《中国人的戏剧》《中国故事集》《黄衫客传奇》《英勇的爱》)。他在这方面的尝试和实践,无疑又担承着一个先行者的角色,并取得了成功。……当时法国文坛的领军人物法朗士等,便是通过陈季同和他的作品一窥中国文化的。”[18]
为“开民智”“求变革”,林则徐、严复、林纾等人以翻译为手段,将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译介给国人,域外新知振聋发聩,启民救国,开启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声,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转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侯官文化即为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启蒙),为中国的进步潮流打开了闸门,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体系作了努力探索。因此,其与中国式现代化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作者为闽江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注:
[1]【德】马克思、【德】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31-32页。
[2]【日】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
《文明论概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页。
[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91页。
[4]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7页。
[5]《清史稿》卷145《艺文志一》。
[6]【美】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11页。
[7]贺麟:《严复的翻译》,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1页。
[8]严复:《与梁启超书》,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八),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18页。
[9]李泽厚:《论严复》,《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62页。
[10]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八),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202页。
[11]严复:《与熊育钖》(七十三),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八),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364页。
[12]严复:《与熊育钖》(七十五),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八),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365页。
[13]严复:《与熊育钖》(七十三),汪征鲁等编:《严复全集》(卷八),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364页。
[14]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下册),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第359页。
[15]阿英:《晚清小说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82页。
[16]【德】夏瑞春:《德国思想家论中国·中文版序言》,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南京:江苏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2页。
[17]【法】巴斯蒂(M.BastidBrugureie):《清末留欧学生——福州船政局对近代技术的输入》,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版,第276页。
[18]蔡登山:《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中学西渐的第一人——被历史遗忘的陈季同”,北京:北京出版社2019年,第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