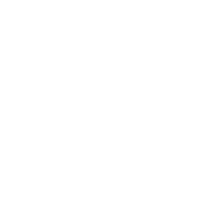难忘初心 致力文史
——记著名史志学者卢美松
林华光
卢美松,1944年10月出生于福州市鼓楼区琼水河东之水部柳宅村,福建著名文史研究和方志编修专家。福建省文史研究馆原馆长,现为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大学福建校友会会长,闽都文化研究会评审委员会首席顾问。曾经兼任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副会长,福建省地方志学会副会长,中国地方志协会理事,福建省历史名人研究会会长,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副会长,福建省外大学校友会副理事长,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副会长,福建省炎黄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
他幼年开蒙于私塾,1952年至1957年就读于琼水小学(现鼓楼第五中心小学);1957年至1958年,初中一年就读于福州十一中,因“大跃进”中的教改,中学改为中专,便转学到福州十五中;1960年保送入福州高级中学,完成高中学业;1963年至196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史专业。
大学毕业后分配留北京,1969年1月赴北京军区农场(山西洪洞县)劳动锻炼。1970年8月回北京,再分配到大兴县芦城人民公社工作。1973年3月任教于大兴县委党校。1976年2月调回福州,先后任福建省财政厅人事教育处干部、副科长、副处长。1985年8月任新创办的福建财会管理干部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1994年3月起调任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编审)。2004年6月受聘为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长(2011年10月受聘为馆员),2014年7月退休。
他长期从事福建地方志编修、地方历史文化和人物研究。个人主要著述有《中华卢氏源流》《中华姓氏谱·卢姓卷》《福建北大人》《福建历代状元》《闽台先民文化探源》(合作)《福州名园史影》《朱紫名坊》《坊巷名居》《闽中稽古》《芸窗谈故》《松轩话史》《薇圃掬露》《芸编留简》。另主编有《严复翰墨》《福州双杭志》《书坊乡志》《福州内河史话》《福州鳌峰史话》《冶山史话》《沈葆桢研究》《榕台关系研究》等。
1994—2004年,在福建省地方志编委会工作期间,分工主持《福建省志》各分志编修,主编省志《人物志(上)》《福建历史地图集》《武夷山志》等。同时负责新旧志书、年鉴和各种文史书籍的编辑出版,共计印刷198部(其中省志78部)。
2004—2014年,主事福建省文史研究馆,主持出版《福建文史丛书》及其他著作109种。2007年以后,分别主持国家课题(子课题)《台湾族群迁徙地名研究》、国家文化建设工程之《中国地域文化通览》“福建卷”“台湾卷”,省级社科规划课题《全闽诗录》《八闽文化综览》。
2014年7月,卢美松年届古稀,卸任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长职务,却并未停下文史研究和史籍编纂的忙碌步伐。退休但未赋闲,依然每天“上班”,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文史课题研究、专业咨询、组织课题,其顾问和编书任务迄未止步。
卢美松自小志趣钟情文史,并以此作为终身事业和精神寄托。他感知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精彩睿智,认为“文史是智者的砺石,惟有坚忍者可以磨砻造就。”从1994年专门从事福建地方志编修开始,足迹踏遍八闽每个县市和众多乡村,经手编辑出版各种史志著作近三百部,因而获得“福建史志百科”的美誉。

卢美松在福建省首届“福”文化论坛上接受记者采访(毕耕 摄)
在内容博赡的文史丛林中,他满怀对乡土文化的深厚感情与敬畏之心,以过人勤勉和不懈努力,或编书,或著述,或论文,或研史,或撰序题跋,皆为文史而作。究其原因,均缘于文史爱好的初心,不能忘情于传承乡邦的文运史绩。他在思索“社会的自然进程就是经济发展带动文化进步”之深意,三十余年没有一天离书搁笔。他说,“‘小草恋山,野人怀土’,夙愿与职责都敦促我守望这片故土。”作为北大学子,他景仰首任校长、乡贤严复,决心以自己所学服务家乡,实现古人“敬恭桑梓”的宿愿。
一、智窦初开迷旧学
卢美松出生于福州东郊农家。因时艰家贫,又是家中长子,很小就开始农务与家务的劳作。幼时喜看闽剧、听评话,常听老人讲地方故事。
六岁入私塾,“智窦初开”:每日课诵《三字经》,描红字簿等,学海初泛舟,开启了对神秘知识世界的求知渴望。
他一直谦称自己读书觉悟晚、起步慢,小学阶段只知看童话、寓言、民间故事。甫上初中,到校图书馆借阅《红楼梦》,管理员给了他一本繁体字版的《石头记》,当时很觉诧异,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同一部书。从初中开始他爱看古典小说了。
少时,其父购置的旧木屋厅堂和楼房楹柱上贴满红纸对联。上小学以后,方认得字是“户枢不蠹;流水不腐”,“民生在勤;德行唯俭”,“杯酒纵横廿一史;炉香缭绕十三经”。许多年后解得其意,才知这户房东原也是书香门第。他庆幸称,大抵是因为生长在这里,沾了这户人家的文气,从而走上读史从文的道路吧。
现在无从追寻他何时埋下喜好文史的种子。不过,据他回忆,初中时初见《汉语》《文学》和《历史》教材就心生好感。让他记忆清晰的,应该是在初一开始接受的“诗教”,从此深深迷恋上中国传统文化。
记得初中始读唐诗“两个黄鹂鸣翠柳”,语文老师边朗读边用彩色粉笔在黑板上描绘:黄鹂、翠柳、白鹭、青天,十分好看;老师还用福州方言吟诵“秦时明月汉时关”诗。他首次震撼于古诗境象之美,努力记诵。他至今还能背诵出明代散曲家王磐的《朝天子》课:
“斜插,杏花,当一幅横披画。毛诗中谁道鼠无牙?却怎生咬倒了金瓶架?水流向床头,春(花)拖在墙下。这情理宁甘罢?那里去告他,那里去诉他?也只索细数着猫儿骂。”
多年过去,卢老闭起眼睛都能感觉出这么一幅生动的“横披画”。你看,老鼠咬坏瓶架、拖走花枝,主人却告诉无门,只得斥骂猫儿,这情景何其生动有趣,只是所含社会讽刺意义则尚未索解。还有一首元曲《咏喇叭》,他同样背得出,只是当时也未解其讽刺意味。有趣的还是辛弃疾的词:“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满目诗情画意,都是在乡野常见的景象。特别是老师讲解“平冈细草鸣黄犊,斜日寒林点暮鸦”——山坡上,小黄牛正吃着嫩草;早春的傍晚,树林枝头点缀着几只寒鸦,生机勃勃,情趣盎然。卢老忆说这些便陶醉其中,连称“这是何等美景啊!”
他记得老师详细讲解何为写“点暮鸦”:因为黄昏时分,远望树梢乌鸦只剩一个黑点。这种场景也是他在家乡的田园岁月所习见的。他经常在黄昏时候出神地佇望着邻村荷宅大樟树上聒噪的暮鸦。诗歌意象甜美,描绘生动,让他永生难忘。少年不识愁滋味,唯觉桑梓美如画。老师的“诗教”引人入胜,让他入门之后从此不能自拔。
他说不敢自称“好古敏学”,但笨鸟勤习,有助于飞;手不释卷,嗜读古史、古诗、古文之癖形成,致力于斯,也受益于斯。
二、进学高地爱古典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上学经历,所以对母校的记忆,就成了人生回忆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高中阶段是他进学成长的关键时期,又是处在特殊的年代之中,所以是永远不能抹去的历史记忆。
“予生也愚鲁,进学的滥觞始于蒙塾,学近两年似乎尚未脱蒙;到小学读了6年,才算扫了文字盲,不仅会认课文,而且开始爱看课外读物。循此继进,初中三年更多读一些文学书,尤其是古典文学之类。”他说自己的读书经历中,真正算得上看书学习、受教获益的只是在福州高级中学的三年。
1960年,卢美松初中毕业,正在整理书籍和笔记,准备应付中考,没成想班主任竟通知他们几个同学“保送上高中”,让自报志愿。他们几人少不更事,只觉免考升学是大好事,喜之不尽。因为胸无大志,自惭形秽是乡下人,当然不敢报福州一中、三中之类名校。大家凑合集议,一致同意班主任的建议报“福高”。其实,他们对这个学校全然无知,校名是第一次听说,地址在哪里更不知道。及至后来结队寻访,经台江、过大桥,从仓前街登山路,上了烟台山顶,才知道福高原来在洋人办的教堂边上。校名虽新而校舍甚旧,听老师介绍才知道,这所学校创办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1年,本名福州工农速成中学,1956年定名为福州高级中学。其校址原为福州鹤龄英华书院,其古老校舍的原建筑则可以追溯到1881年建的鹤龄楼、施教楼(书院的美志楼)、1905年建的力教堂(书院钟楼与礼堂),可见其古老。
年少不知苦。上学的路程从自己家(水部柳宅村)到福高,光着脚丫快步走至少也得9个字(45分钟)时间。那时没钱,一趟8分钱的公共汽车是坐不起的。天天早出晚归,中午在校寄膳,也不觉苦累,只是觉得饿。高中三年,从1960年至1963年,正是“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忍饥挨饿的读书是“苦学”。但对他而言,最快活的是获得了“悦读”机会。因为行走约一年后,学校为保证学习效果,规定城区学生也要在校寄宿。这对他而言是天大好事,可以免却日日来回奔波之苦,而且有了更多的看书时间。因为农家子弟放学到家,一放下书包就要拿起家伙做家务,或到田园干农活。晚上为节省煤油,做完作业就要吹灯上床。所以在家要读书是很难的,只有在校课余抽空看,甚至上课偷着看,或在上学、放学路上边走边看。“寄宿了,家里要为我每月单独付出8元4角的伙食费和28斤粮食定量,而且少了半个劳动力,会给父母增加不少劳动负担。”
卸掉家务和农务的重担后,在福高专心致志地读书,真是快何如哉。那时大家吃不饱饭,体育课只做小运动量的活动,打打简化太极拳;考试也很少,记得一个学期下来只考物理一门;作业还是有的,在“自修”课内即可做完。有人自嘲说,饿着肚子读书更容易入脑,记得更牢。有了空闲也就有了更多读书的时间,他吃过饭就到阅览室看书,下了课还是看书。“学校图书馆成为我的好伴侣。阅览室是我每天必去的地方,因为报纸天天换,期刊多又常更新。那时的许多刊物,如《知识就是力量》《旅行家》《新观察》《热风》《诗刊》《福建画报》等等,都是我喜读的书刊。当然,馆内大量藏书才是我的最佳选择。”在两年多时间里,他选读了大量名著,不仅有人们熟知的古典名著、章回小说,而且有外国名著,如前苏联的、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等等。说实话,对外国那些陌生而拗口的人名、地名,实在没有记忆的兴趣,倒是我国古典文学的诸多名篇,读后令人神往而且神旺。不仅唐诗、宋词、元曲读来朗朗上口,一咏三叹,感觉美不胜收,就是诗经、楚辞、汉赋、诸子的文章,也觉咀嚼有味,令人有会心之悟。所以当时一面费心抄录,一面记忆背诵。说也奇怪,可能由于兴趣,精神专注,加上那时记忆力稍好,对别人不大感兴趣的古典文学,他却兴味盎然地读着,用繁体字抄写,以致同学有叫他“老古董”“活字典”的。当时对《论语》《孟子》之书,通篇熟读,记诵名句,自认为有助于高考的文言答题,算是有点“功利心”的算计。“语文老师告诉我,如《庄子》之书,将来上大学以后再与你一起讨论研究,那文章汪洋恣肆,颇难索解。”看来老师也似乎认定他会考上大学的。正是因为他对文史方面的兴趣和挚爱,所以特别留心于语言(包括所学俄语)、文学(特别古典文学)、历史、地理乃至外国历史与古代天文知识等等,多有涉猎。真是“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光华灿烂,冉冉上升,俗称积学储宝,庶几近之。当年所学,至今在作文、演讲时尚能不经意间用上。
“兴趣是最好的导师”,此言不虚。“正是兴趣导我推开知识之门,又是兴趣引我循着知识之阶攀升,登堂、入室。”他读书且思考,进步明显,故有自信。自觉有了超越一般同学者的知识积累之后,在决定命运的高考中一搏成功。其实对他而言,那场高考是没有多少悬念的竞赛,那时考生填报高考志愿是由班主任和课任老师们集体会商、统筹排定的。他只是对班主任的决定作一点小的修正,即把报考文科最高学府的志愿,前后顺序稍作调整:将排在前三位的系科东语、西语、俄语三系挪后,而将他所心仪的中文、历史、哲学调前就是了。他的理由很简单,福州人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说外语怕更不行,老师自然没有异议。他的执着还在于,在填报“志愿表”的“备注”栏中,加上四个字说明:“酷爱文史”。“这可能是随意之举,无心之笔,但却因此改变了的他命运。最终正是因为历史卷成绩最好而被录取于历史学系。”还有什么比遂愿更让人振奋的呢!既是天遂人愿,也是人遂人愿。
应当承认,他的遂愿是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摒却人所共嗜的爱好和欲望。须知他是在渴求中获得读书机会的。初中以前,因家无储书又身无分文,故而未得充分阅读的机会。家务、农务的繁忙,也令他不得看书的余闲。当然,为读书他也有自己的小算计,如借人书籍抢时间看,无钱租书从图书馆借阅;就是在寒暑假帮家里挑菜上街去卖,归来时看天色尚早,便径直走进福州体育场,放下担子,在空无一人的主席台上独自枕着扁担高卧看书。这时只觉凉风习习,书香阵阵,惬意极了。可惜好过的时光总是太快,不觉日上中天,腹枵难耐,该回家了。如此读书,至今想起,仍觉有味。还有印象深的,就是15岁那年,刚上初二,借得《东周列国志》,喜之不尽,爱不释手;帮大人在灶下烧火时还在读,大人的责备也充耳不闻。因为读书,也有舍弃,如福高校舍地近烟台山炮台,每到周末,守台炮兵放映电影,许多同学都趁机免费蹭观,而他却始终无动于心。即使是当时最轰动的热门电影《红楼梦》,招待毕业班同学的,也仍然不为所动,还是在上大学后才补偿饱了眼福。高中的读书时光真好:清晨在校园树下默读、背书;夜晚在教室里看书、抄书;劳动课在市郊种菜施肥,为救饥荒随老师上山摘野果做代食品。有大唱革命歌曲的豪情,有学习雷锋精神的善举;没有轻歌慢舞的闲情,更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
在那金钱和物质都短缺的年代,读书人多有不堪的尴尬。记得一次在仓前街边旧书摊上,看到一本厚厚的《红楼梦研究论文汇编》,心痒欲购,无奈阮囊羞涩。急中生计,低眉悄声问老板:“可否用粮票换购?”老板一愣神,端详一下,竟痛快答应了。于是以一斤饼票的代价,换得这本“宝贝”。在福高上学的日子,他最常去的书店就是观音井新华书店、大桥头新华书店和中亭街旧书店,那里都是他淘书的好去处。一次在中亭街旧书店看到一本破旧的四角号码字典,1954年出版的,标价1万3千元(合今1元3角),只售八角钱,他当即买下,使用至大学,不忍释手。可惜那时书店中他想买的古典文学和历史类书实在太少,只能守望着购买《中华活页文选》,一期不拉地将其装订成册。这本书使他增长了许多古典文学知识。
福高是实现个人梦想的起航点,是一块进学高地。这不仅因为学校地位清高,仰望头顶繁星,俯视闽江清流,烟山之巅更有一批“高人”,就是有真才实学又各有专长的老师:不管教的是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乃至俄语。他们又正当盛年。特别令人敬重和感动的是,他们中一些人还身被污名,背负沉重的精神包袱,但于教学却都无一例外的敬业,真正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为怕有遗漏,我只能在心中铭记而不能一一道出他们的名字。要知道我们都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攀升的,我们的寸进,都是他们力挺的结果。”卢美松深情地感慨说。
福高是他学习的福地,学业的长进,知识的积累,都从此地跃升,而且所学受用终身。当时的“初积”仍然是今天“薄发”的资源。在那个年代,好读古书者鲜少,即使能坚持在校读书也属不易,这是时代的无奈。记得1960年初进福高,高一年段有十个班,总人数当在500人上下;一年以后,就撤销了第一班和第十班,因为退学人多;到毕业时,就连8个班级中各班的人数也只有四十人上下,最后报考文科的居然只有一个班。当年福高的高考录取率在全市算是拔尖的,考上名校者不少。他读书理想遂了愿,也为福建的“高考红旗”添了彩,值得庆幸。“当然,我的读书生涯不止于高中阶段,这只是一段进境;嗣后的大学五年,才是我从福高出发的目的地。”
身在仓山之颠,远望苍穹,俯视滔滔,其眼界和胸怀自然不同。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一点不假;从这里再出发的他,可能已不再是“吴下阿蒙”。为了答谢母校的栽培,特别是校图书馆赐予他的知识甘露,他为回馈母校,捐赠了许多自己的藏书。而母校福高的进境也大胜昔日,现今高中生三个年级38个班,近2000学子,较他们当年壮大了许多倍;而且在教育资源分配未均衡的情况下,母校仍取得骄人业绩,延续着昔日辉煌,怎不令人欣慰?他回母校讲座,勉励后辈学子,更能珍惜流光,珍重自爱,努力成才,为母校争光。
三、读书疗饥恋文史
卢美松坦言,在初中才正式喜欢上文学和历史。初二时的一本《中国上古史演义》普及读物导引他坚定了自己的志趣。
书是同学向他推荐的。他如获至宝,一口气读下来,令少年的心深感震撼:原来中国在上古时代,有这么多历史人物与传说故事。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精卫衔石填海、伏羲兄妹成婚、王母宴请穆王,还有夸父追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后羿射日、嫦娥奔月,更遑论黄帝战蚩尤、刑天舞干戚等精彩而又生动的故事。
“真是光怪陆离,惊心动魄,闻所未闻,令人神往。”他惊叹于“中国历史之悠久和中国神话之精彩。”他的好奇心与求知欲一起膨胀。此后,已远不满足于榕树下听评话,课堂上读古文,也不满足于课堂上老师的讲授,开始自辟蹊径觅书静读。
他广搜博览,无论是《隋唐演义》《说岳全传》还是《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也无论是《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还是《包公案》《彭公案》,凡是能找到的古典小说,通通寻读。高二开始寄宿福高,全身心沉浸在阅览室、图书馆。不论是流行刊物,还是现代名著、古代经典。
谈及对史书的“痴迷”,一件事让他终身铭记。初二时奶奶留给10元临终“手尾钱”,币纸崭新,亲人情重,一笔“巨款”珍重宝藏。但不久,还是被他“大手”花掉。
当时高桥头有一书摊,他没少在此流连过。一次看到有一部崭新的《封神演义》,上下两册卖价5元,他数度徘徊桥头,最终咬牙把书买下,即用报纸齐整地包好封皮,诚敬捧读。
“真如饥不择食,唯恨家无藏书。”这是他对中学年代的深沉记忆。卢美松笑道,那时他喜看课外书在班上是出了名的,以致在高考前的“升学指导”课堂上还在“私读”课外书,被巡视的老师点了名。
卢美松博闻强记,娴于辞令。记者采访中,有的诗词至今仍可随诵,如60年前初中时所学《诗经》的《小雅·采薇》还能朗朗诵出,回忆历史课老师释读《诗经》“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的诗意时,说明这是从军戍边战士的恋爱思归之作,并指出“莫”字同“暮”,还演示甲骨文的写法与字义,这种教法与后来大学老师的“说文解字”教法异曲同工。文学老师吟诵“不教胡马度阴山”时,特别指出此处“教”字应读平声。这些都令他深感汉字、汉语的精微奥妙。
他由此初知汉语造字的规则和精深内涵之所在,激发他去追寻更多的典故轶闻,尤其注意于古文的注释及字音。他说,特别喜欢边读古文(或古典小说)边认古字和典故注释。他还仔细阅读并抄录《六朝文絜》中的人物和诗赋。由于好写繁体字、爱读古诗文,同学笑称他是“老古董”。
他说,当时的这个爱好,让他获益不浅,迅速提升了文史的成绩,尤其萌发了对语文史地类学科的兴趣。这或许在冥冥之中注定了他今生与文史结缘。
诚然,钩沉记忆忽略细节,他引以为豪的还是在得知录取后旋即想起的《神童诗》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庆幸有了晋京深造的机会,实有古人跃龙门、折月桂的快感。回想求学不易,期间有食不果腹之忧,却常以“须信读书可疗饥”自勉。
四、岂为功名始读书
1963年夏,卢美松庆幸遂愿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但父母似乎颇不理解,无奈地问:“学历史将来干什么?”他只随口答:“可以教书吧。”因为那个年代人们热门向往的是搞科技,当工程师。到校后,他的文史兴趣迅速得到升华,最高学府的教育,激发他更高的读书目标。
卢美松当初选择中国史专业,还有一件趣事。彼时北大历史系有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三个专业,他和高中同班同学欧潭生(后亦成为省文史馆馆员)同时考入北大历史系,选择专业时,欧潭生怂恿他一起上考古专业,说“学考古有机会游山玩水。”卢笑笑说:“我不想去挖墓,也怕见棺材。我还是喜欢钻故纸堆,看我的古书。”
忆及北大经历,卢美松感叹:“上天对自己颇为眷顾,当时无论在中文系、历史系,都聚集着全国最优秀的学者。”副校长、历史系老主任翦伯赞教授,在新生入学教育时为他们打开蒙昧的心扉,坚定专业的信念。“这位名重史学界的长者,谆谆教导新生,要热爱史学专业,树立专业理想,刻苦读书,报效祖国。”长者旁征博引,举例说明读史的用处,饱含拳拳之心。
他回忆张传玺讲师讲授汉史的情形:用浓重的山东口音朗读《汉书·食货志》的精彩段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纯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并且屈指申教:史书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形容汉代商品经济发达,经商者众。老师的释说鲜明生动,至今难以忘怀。令人难忘的还有唐史副教授汪籛神采飞扬地讲述隋唐文化,边说边写,自称能背万首唐诗;周怡天老师手持卡片,笑声朗朗地讲述古埃及法老历史;福州老乡邵循正教授沉稳而又耐心地娓娓讲述忠王李秀成的事迹;中文系助教蒋绍愚以标准的浙江口音解读《诗经》“风雨凄凄,鸡鸣喈喈”名篇。当时职称不高的教师,后来都成为大家名师。
研究地方志当时或许还不是卢美松的旨趣。他因仰慕北大图书馆的丰富典藏,满怀好奇心去借阅在家乡早已听说却无缘谋面的《闽都别记》,不料,管理员给他的竟是《闽都记》,粗略翻阅后才知是地方志书。“当时感到索然无味,何曾想到,这正是三十年后我开始从事的职业。”卢美松笑道,“这趟借书也许是冥冥之中对我的一个暗示吧。”
北大毕业后,卢美松分配留在北京,但并未从事与文史研究有关的工作。他先后在山西洪洞县、朔县和北京市大兴县等地从事劳动锻炼和行政工作。由于气候水土不服,1976年2月从北京调回福建,在省财政厅工作。那时他住的单位宿舍就在冶山欧冶池边。这触动了他的心思:“历史再一次提醒我,应该为福州、为福建的历史文化做些什么,才不辜负自己当年的志愿和所学专业。”
他回顾这一段基层和机关工作时说,“一切经历皆是财富。人生罕有坦途,坎坷践履,丰富阅历,磨砺意志,积累经验。我们这代人有过‘文化革命’的思想迷惘,也有工作错位的命运乖舛,但依旧靠初心拨正航向,靠读书取得进境。书籍成为超度沉沦的慈航。”
在后来的追忆中,他称此生的运命、作为应当归功于读书之力,“书籍成为步入人生坦途的舟车舆马。”他庆幸地说,“读书获得成功的快感与弱冠之年的自信同在。”正因此,上级领导考核时问他:“你身在财政,却仍读史书,写历史文章,调到文化部门如何?”他痛快答应,且选择地方志,因他认为这是用史多的地方。
卢美松长期从事福建地方志编修和历史文化与人物研究,尤其钦佩古代乡贤中循吏清官的惠民之政与高风亮节。他在为《闽东历史清廉人物》所作序言中引用古代闽都士人的诗称:“人生所宝惟令名,一士远胜王侯荣。”认为那些清廉人物正是由珍惜气节而博得令名,他们除了具有一般循吏的“清、慎、勤”优点之外,还各具良好禀赋并作过独特贡献。他们都以有限的生命、短暂的仕历,为后人树立了永久的丰碑。他们或立身廊庙,辅佐君王,鞠躬尽瘁,建树辉煌;或执政临民,造福一方,黎庶铭感,永志不忘;或立功异域,血洒疆场,马革裹尸,百世垂范;或饱学博识,富有文章,传道承统,勋名同光。
他曾在著作自序中写下对人生宏愿的理解:“古人‘三立——立德、立功、立言,都不可以离开读书。”认为自己浪得微名,也是沉潜读书与埋头笔耕的结果。他深信“人生所宝唯令名”,所以有“鸟爱其羽”的谨慎。
卢美松引经据典阐述己见:“古之出仕为官者,虽皆饱饫圣人之教,深受家国之托,但人各有志,途生歧异,正邪相对立,冰炭不相融。持守善道者,立定志向,守身如玉,扬名寿终;或为及时行乐,蹉跎岁月,一事无成;或为贪权弄贿,丧心病狂,身败名裂。荣辱两途,天壤之别。有志者自当谨身惜缘,常思报国爱家;有为者更应奋勉精进,谋大众百世大利;洁身爱羽,踵先贤千秋风范。”
五、回归方志称“百科”
1994年,他在晋升时选择了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称“终于回到早年想望的人生轨道上来”,由此开始了工程浩大的十年修志工作。他称这是自己人生旅途的新跋涉。
他开始为编书而读书、为写作而读书的人生新旅程。“十年编纂甘苦备尝,其成就感与读书乐相融为一。”他说,从当年的爱好变为现今的职业,自然乐此不疲。
1994至2004年,他在福建省地方志编委会主持省志编修并负责志书、年鉴编辑出版工作。他相信,编修地方志正在于实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目标。他负责编审的志书仅省志部分,字数就以千万计,涉及诸多专业部门,堪称“百科全书”。他又勤于下乡,爱好做社会调查,了解各地的历史、文化、人物等舆情,为此他跑遍了全省所有县、市、区以及许多著名乡、镇、村,书卷与行程均在万数以上。在省地方志工作期间,他与同事们共同努力,主持112部省志分志的编修,经手共计出版70多部省志,还有其他志鉴及文史类图书100多部。
2004年,正当花甲之年,卢美松又应福建省政府之聘,出任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长。这正应当年“酷爱文史”的期许,因而又有了新的读书追求与写作使命。他再次感悟到读书创造机遇的道理,深切感悟“书籍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与进身作为的动力。”
2007年以后,他陆续主持国家课题、省级社科规划课题以及福州市乃至区县委托的课题。他主事省文史馆期间,组织整理出版大量文史著述,业绩累累,见于书籍,载诸口碑。在他主持出版的《福建文史丛书》系列图书109种中,大多数是已故馆员和乡邦文史专家的遗著或专著,他也因此赢得文史界和出版界的赞誉口碑。他还经常应邀参加社科类的学术研讨、咨询评审,参与此类文化活动的主持或宣讲。对这些文史活动,不惮劳烦,始终持热心参与的态度,也是出自“报效桑梓”的初衷。
2013年6月,见诸报端的一篇名为《画一幅精细绚丽的八闽历史文化地图》文章,引起全国文史界的注目。该文介绍新出版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福建卷》,对福建文化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作了全面归纳和概括介绍。他主持“福建卷”的编撰,书稿一出,即得到中央文史馆馆长袁行霈的肯定和国内评审专家的赞许。继而又扩充出版《八闽文化综览》专著,向世人展现精细的福建历史文化版图,成为业内研究闽文化绕不开的参考书。
卢美松深信“读”和“行”的治学理念。从1994年从事福建地方志编修和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开始,他就注意在省志各专业分志的指导和评审中学习修志专业,汲取知识营养,同时注重实地考察,下乡调查。十年间足迹遍及省内各地,自编或指导编纂《福建历代状元》《建阳书坊乡志》《闽安镇志》《武夷山志》,认真指导并推动部门和地方修志。人们誉称他为“福建方志百科全书”,他诚惶诚恐地认为,这是过誉之词,愧不敢当,因有大师在前头,“典型在夙昔”,自己不过是“廖化作先锋”而已。在主持省文史馆的十年工作中,他同样重视社会调查和为基层的文化工作服务,包括文物调查和保护、博物馆展览陈列、历史人物研究纪念、中华老字号评审、古地名考证、地方历史文化研究、闽台关系研究等等,虽届高龄,仍乐此不疲。可贵的是,每到一处,都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不计报酬,不惮劳苦,平易近人,因而广受好评。
卢美松认为,没有文化自觉难以保护好古建筑。他正是以这种文化自觉,主持福州“朱紫坊文化研究”,最终结题并出版《朱紫名坊》20万字图书,继而主编出版《福州双杭志》《冶山史话》《福州内河史话》《福州鳌峰史话》等书。他在接受人民网记者专访时说,要吸取三坊七巷经验,应当全面、完整地保护历史文物、名胜古迹。如果有修缮,应按“修旧如旧”的原则,这是底线,应避免过度商业开发。人人形成文化自觉,保护文化遗产才不会是空话。
六、笔耕不辍证初心
面对如此丰富的创作及研究成果,若追问其从事地方史志研究的诀窍,卢美松郑重地说,文史之学,内容博赡,课题俯拾即得;关键在于“用心勤”且“用志专”。
谈及为何矢志于此,他说:“因为我的夙愿与职责都敦促我守望这方故土文化。”他说,守望源于眷念,所谓“小草恋山,野人怀土”,不仅为系念乡愁,更为厚重的文化;写作是为了报效,不有曰“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所以敬畏并热爱乡土文化。
实际上,从事多年地方文史工作,卢美松也在思考如何传承和弘扬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他认为,“处今之世,建设日新月异,城乡沧桑巨变,而人们追怀历史、守望文物的情绪与日俱增。”他热心地带助手,开讲座,助力市政文化建设,指导学术研究与社会文化活动。
他在职用笔甚勤,因为责有攸归;而今动笔仍频,盖由积习使然。或论文,或述事,或序跋,皆情注文史。并无功利之心,诚所谓“不因果报勤修德,岂为功名始读书”。修德、读书皆来自自觉的行动。卢美松坦言,就志趣而言,钟情文史,是因它他将读书与写作看作日常的生活方式,老来又是养生的手段,也是自己的精神寄托。他常言“文史缘同骨肉亲”,因为从中可以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精彩睿智。正是这种感知,使他终身倾心,义无反顾。大学一年级古汉语老师讲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含意,触动了他的深心,因此他深信“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就是他兢兢业业、矻矻穷年地热衷文史的缘由。
作为北大人,他表示十分景仰曾为母校作出特别贡献的两位乡贤:张亨嘉接掌京师大学堂,训勉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开创优良学风,其梦想在于造就近代新型人才;严复首任北京大学校长,挽上黉于将倾,扬声名于宇内,力主“兼收并蓄,广纳众流”,其梦想在于建构“一国学业之中心”。
卢美松说,先辈们把梦想留给北大,圆梦却在后人。“我进入历史系或许正是乡贤们在冥冥中为我点燃梦想之炬,圆梦之行虽然艰辛却很甜美。有生之年我还将继续笔耕,为弘扬闽文化蜡炬成灰,克尽绵力。”
从事史志编纂与文史研究,卢美松没有也不曾想搁笔离书,这正是源于不能割舍的文史爱好,也是不能忘情于乡邦的文运与史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