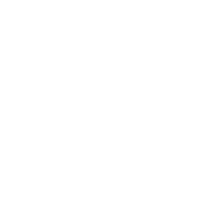·福建海洋精神”专题·
07.海洋精神的物化:闻名世界的刺桐海船
宋元是我国历史上造船业和造船技术大发展的高潮时期,“海舟以福建为上”,福建造船业及其制造技术在当时中国和世界占有领先的地位,也是宋元福建海洋精神物化的杰出代表。
一、泉州湾出土的宋代海船
1974年和1982年,考古工作者分别在泉州后渚港和法石港发掘出两艘古船,从而拉开了福建宋代海船实物研究的序幕。
发掘出土的后渚港古船(以下简称“后渚古船”)位于东经118°59′,北纬24°91′,距滩上2.1-2.3米,距古渡头135米,沉埋在由宋元青釉和宋代黑釉瓷器残片、宋代铜钱、香料木、船木、竹编、绳索残段、锈铁钉、鸟兽骨等包含物的宋元堆积层之中。船体甲板以上部分已荡然无存,只残留一个船底部。船身残长24.2米,宽9.15米,深1.98米,平面扁阔近椭圆形,尾方。船壳为二三重板结构,船内分为十三个隔舱。从船底形状以及第一舱、第六舱分别保存的头桅和中(主)桅底座看,该船是一艘尖底型的多桅船。古船残体尚涂有白灰,底部的龙骨两端结合处凿有“保寿孔”,中放铜镜、铜钱,其排列形式为“七星伴月”状。“七星”是代表“七洲洋”(指现在的西沙群岛),因这一带多礁石,是航行的危险区。铜镜象征着光明,表示祈求安全通过这个经常触礁沉没的危险区。

泉州湾出土的后渚古船
伴随着后渚古船出土的文物很丰富。船上用品有桐油灰、灰括、铁钉、钉帽、铁板和麻绳、碇索、竹编等。助航工具有木桨及水时针,隔舱板和底座等。根据出土海船残船体以上底层堆积情况、海船船型与结构特点、船舱出土遗物以及沉积环境等方面的考察和分析,后渚古船系南宋晚期的中大型远洋货船,航行于东南亚一带,估计是停泊时,遭到意外不幸而沉没的。(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报告编写组:《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10期)
1982年试掘的法石港古船(以下简称“法石古船”)船体残破也比较严重,与1974年出土的后渚古船比较,法石古船在造型、结构、工艺与用材等方面与后渚古船有不少类似的地方,但法石古船也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说明法石古船与后渚古船年代相去不远,应同属南宋晚期福建制造的远洋货船,但与后渚古船出自不同的造船厂商,或年代更晚些。(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等:《泉州法石古船试掘简报和初步探讨》,《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年第2期)
泉州湾宋船的出土,是我国造船史上一项重要发现,亦为我们研究宋元刺桐海船制造技术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
二、刺桐海船的多项创新
由于海外贸易的日益繁荣,宋元时期我国所造的海船,无论在坚固性、稳性、适航性,还是水密隔舱的广泛应用等,在世界上都具有先进性。“海舟以福建为上”(〔宋〕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卷一百七十六),这句在宋元广泛流传的评语,说明以刺桐海船为代表的福建海船在我国造船史上具有领先地位,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船型设计、重板船壳、水密隔舱、多桅船帆、航运设备、造船用材和联接工艺等方面。
1.适航的船型设计
宋元时期,我国船舶的船型已经定型,其中以福船、沙船、广船最为著名,被称为中国古代的三大船型,而应用最广、影响最大的要数福船。关于宋代福船的船型特点,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描述说:“其制皆以全木巨枋挽叠而成。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四,客舟)徐兢曾于北宋宣和四年(1122)出使高丽(今朝鲜半岛),率领由福建客舟和“神舟”组成的船队往返中朝两地,因此他对福建海船的描述是较为可信和准确的。此外,《宋会要辑稿》也有福建所造海船为“面阔三丈、底阔三尺”(〔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之一八,船,战船附)的具体记载。结合泉州湾出土的海船,可以看出以宋元刺桐海船为代表的福船具有底尖、船身扁阔、长宽比小、平面近椭圆形等船型特点。这种船底尖、船身扁宽的设计,使海船便于破浪前进,在遇到横风时横向移动也较小,适于在风力强、潮流急的海域航行。另一方面,宋元刺桐海船在龙骨和肋骨的设计上也充分考虑到航行环境。后渚古船的龙骨是由两段粗大坚实的松木结合而成,贯穿整个船身底部,增大了船的纵向强度。而在隔舱板与船壳板交接处,都服帖着用粗大樟木制成的肋骨。这些肋骨与底部的龙骨组成一个坚固的立体三脚架,增强了船体的横向强度。尤值得一提的是,后渚古船船长中点以前的肋骨,都装在隔舱壁之后,而中点以后的肋骨又都装在隔舱壁之前。这种既考虑到船体的横向强度,又顾及结构排列整齐的做法,同近代船舶设计理念如出一辙。
此外,在船壳板细节设计方面,后渚古船船底两边壳板各外扩成四级阶梯状,使海船的回复力矩增大,有利于抗御横向波浪的冲击。还有体外龙骨的设计,其与尖底造型和四阶外壳板构成一个完整的防摇系统,使海船具有较强的稳性。
2.实用的重板船壳
关于刺桐海船多重船壳板的应用,中外史料皆有记载。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明确指出泉州造船时“有二厚板叠加于上”,并进一步指出刺桐海船修理时还可增添船板,“此种船舶,每年修理一次,加厚板一层,其板刨光涂油,结合于原有船板之上……应知此每年或必要时增加之板,只能在数年间为之,至船壁有六板厚时遂止”(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三卷第一五七章)。在这里,马可·波罗谈到刺桐海船船壳结构的两个特点:一是船壳在建造时基本结构是二重木板;二是船体每次大修时贴一重板,最多可大修四次,贴到六重板。国内文献也记载道“凡海舟必别用大木板护其外,不然则船身必为海蛆所蚀”(〔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海蛆)。马可·波罗等人记载的刺桐海船多重板船体结构,已为1974年泉州后渚港出土的宋代海船所证实。该船船底用二重板叠合,舷侧则用三重板叠合。后渚古船沉没时间与马可·波罗到刺桐港的时间相距不远,说明宋元时福建用多重板建造海船是较为普遍的事情。
刺桐海船船体之所以用多重板,是因为尖底造型的船壳弯曲多、弧度大,采用此建造模式不仅取材和施工(包括维修)较容易,而且使船壳坚固耐波,经得起狂涛巨浪的冲击,有利于远航。此外,多重板船壳还有防海蛆浸噬和抗礁石撞击的功能,这些都是我国古代造船匠师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具有时代的先进性。当然,1982年试掘的法石古船底板为厚重的单层松木,说明宋元时期刺桐海船不仅有多重板船壳,也有单层板船体,一切从实际出发。
3.先进的水密隔舱
在我国,水密隔舱的设置可以上溯到唐代,并在宋元时期的刺桐海船得到广泛、创新的应用。马可·波罗曾记述说:“有若干最大船舶有内舱至十三所,互以厚板隔之,其用在防海险,如船身触礁或触饿鲸而海水透入之事……至是水由破处浸入,流入船舱,水手发现船身破处,立将浸水舱中之货物徙于邻舱,盖诸舱之壁嵌隔甚坚,水不能透,然后修理破处,复将徙出货物运回舱中。”(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三卷第一五七章(注甲))水密隔舱板的设置,使全船分成若干舱,个别舱破漏水,不会流到其他各舱,既便于修复,增加抗沉性,且可加强船体结构,有利于船型的增大。马可·波罗的记载在后渚古船得到了证实。这艘可载重200吨左右的宋代海船,由十二道隔舱壁将全船分成十三舱,除舱壁近龙骨处留有小小的“水眼”外,所有的舱壁钩联十分严密,水密程度很高。在海外航运贸易兴盛的刺桐港,水密隔舱设置不仅有助于增强船舶的抗沉性,而且多隔舱亦具有便于货物装卸的优点。
值得注意的是,宋元刺桐海船在水密隔舱设计时增设“过水眼”,使水密隔舱与舱壁过水眼完美结合,充分体现了福建船工原则性与灵活性相辅相成的造船智慧。水密隔舱增强船体的抗沉性,这是造船的基本原则;但必要时可让进入船体的海水通过过水眼在各舱流动,以便自动发挥其调节海船稳定和船首船尾吃水深浅的作用,这是险恶环境下航行必不或缺的灵活性。水密隔舱完整功能的发挥,原则性与灵活性缺一不可,其创制与改进是我国劳动人民对世界造船技术的重大贡献。水密隔舱技术经13世纪的马可·波罗介绍传入西方,后在18世纪得到广泛应用。

还原水密隔舱福船(林配宗供图)
4.独特的多桅船帆
宋元刺桐海船以多桅多帆著称。据《马可波罗行纪》记载,进出刺桐港的大海船最常见的是“四桅十二帆”和“四桅四帆”类型。《伊本·白图泰游记》亦载,泉州、广州造的“大船有十帆至少是三帆”([摩洛哥]伊本·白图泰:《伊本·白图泰游记》,马金鹏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86页)。泉州湾出土的两艘宋船也皆为多桅形制,说明“船舶之多桅原理,为典型的亚洲式”([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土木工程与航海技术》,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10页)。其中四桅多帆是宋元刺桐远洋商船的典型配置。
多桅不仅意味着多帆,而且风帆的形制、功用也不相同。四桅船一般有四张主帆,其他的帆则称辅助帆。主帆形如斜刀,可转动换向采风,也可升降以调节受风面积,又可调动风帆作用力中心使之最佳受力,它们是具有东方特色的优秀风帆。辅助帆则有四角帆(亦称“头巾帆”)或三角帆之分,“大樯之巅,更加小帆十幅,谓之野狐帆,风息则用之”(〔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四,客舟)。它们都是当风力变化或风向不同时,用以调节船行速度的有力措施。主帆和辅助帆,有时多张有时少张,是根据不同航区、不同风力大小而调节的,所以记载中有四桅四帆或四桅十二帆之别。
此外,四桅船舶中的二桅“可以竖倒随意”(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三卷第一五七章)。虽然宋元刺桐海船船桅可高达十余丈,但由于可以自由起倒,所以并不显得笨重和受限。相比之下,当时外国航船的船桅多“不可动”(〔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四,杂志一),显见船桅转轴的安置是我国海船建造中的又一项重要创新。这样,宋元刺桐海船有多桅杆,可拆装;主帆可转动,可升降;又有三角帆或四角帆辅助,就使得帆船在各种复杂多变的海况条件下航行,也能应付自如,安全快速。正如宋人朱彧在《萍洲可谈》中谈到的那样:“海中不唯使顺风,开岸就岸风皆可使,唯风逆则倒退尔,谓之使三面风,逆风尚可用矴(同碇)石不行。”(〔宋〕朱彧撰,李伟国点校:《萍洲可谈》卷二,舶船蓄水就风法)
5.完备的航运设备
关于福建海船的船上设备,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客舟”中有较为详细的描述:“船首两颊柱,中有车轮,上绾藤索,其大如椽,长五百尺,下垂碇石……船未入洋,近山抛泊,则放碇著水底,如维览之属,舟乃不行。若风涛紧急,则加游碇,其用如大碇,而在其两旁。遇行,则卷其轮而收之。”(〔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四,客舟)船首有正碇(大碇)和副碇(游碇),都用绞车控制,是停泊设备。接着,徐兢还告诉我们船尾有正舵和副舵,正舵又分成大小两种,可根据水的深浅分别使用;副舵供海上航行时配合主舵控制方向。此外,徐兢乘坐的官船还在船舷两边缚上大竹作为“橐”,其作用之一是抗拒风浪对船身的冲击,增加神舟的稳定性,“缚大竹为橐以拒浪”;其二是起着水线的作用,“装载之法,水不得过橐”(〔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四,客舟)。橐就是满载的标志,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古代帆船有关水线概念的首次记录。
虽然徐兢讲的是北宋时期的福建客船,但结合泉州湾商船出土遗迹以及法石乡发现的宋元碇石(陈鹏等:《泉州法石乡发现宋元碇石》,《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年第2期),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宋元刺桐商客海船已配有正副木石锚碇、正副大小可升降方向舵,以及用来测量水线的装置等较为完备的航运设备。而在国外,方向舵的使用比中国晚了400多年。
此外,桨的使用在宋元刺桐商客海船上也很普遍。被摩洛哥游历家伊本·白图泰称作“艟克”的大海船,“船上约有二十只大如桅杆的大桨,每一桨前约有三十人聚拢在那里,分站成两排,面对面站着。大桨上系有两根粗绳,一排扯绳摇动大桨,将绳放松,另排再划桨”([摩洛哥]伊本·白图泰:《伊本·白图泰游记》,马金鹏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37页)。当海面风平浪静时,海船依靠划桨前行。据伊本·白图泰介绍,这样设备精良的海船,只有泉州和广州能够制造。
6.科学的造船用材
宋代福建“林菁深阻”(〔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三之六,漳州渝畲),“林烟蓊霭,横属数百里”(〔宋〕梁克家:《三山志》卷四十二,土俗类四,物产),仅《三山志》所载福州地区就有松、樟、楠、杉等木40余种,造船所需的木材极为丰富。长而笔直的杉木可做桅杆,耐水浸泡的松木可做船身,坚硬的梨木可制作舵。其中桅杆上挂帆,要经受数百吨至上千吨的压力,要求最高。一般而言,十丈长的海船,一定要有一根长十丈的主桅,至少需要一棵高达三四十米的巨杉做主桅,否则无法承受海风的巨大压力。也就是说,从早期开始,福建船匠一直使用耐咸、硬挺能造海船船体及各构件的松、樟、楠、杉等作为造船的主要木材,泉州湾出土宋船如此,现代所造木船亦如此。这一点,福建与我国南方另一造船中心广州不同,“盖广船乃铁力木所造,福船不过松杉之类而已”(〔清〕茅元仪:《武备志》,华世出版社1984年,第4775页)。南宋宰臣吕颐浩在品评各地海船质量高低时也关注到木材的作用:“臣尝广行询问海上北来之人,皆云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昌明州船又次之。”(〔宋〕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卷一百七十六)
福建海船能在强盛的南方造船集团中脱颖而出,除优质丰富的木材和选材思路佳外,科学的用材原则和方法也功不可没。从出土的后渚古船看,凡是经受强大压力的构件和部位,造船工匠都采用坚硬的木材。一是在贴近龙骨的二路外壳板,用樟木板使船底坚实耐磨;二是用整根樟木制成艏柱和肋骨,以增大船体强度;三是第一道和第十二道隔舱壁全用樟木板,使之成为有力的防撞舱壁;四是舵承座与桅杆座分别用叠合大樟木和巨块樟木制成,加强了它们对舵和桅的承受力;五是用樟木制成其他干道隔舱壁紧贴船底的一路隔板,既增加了隔舱壁的强度,又达到了防腐的目的。以上事实说明,以后渚古船为代表的刺桐海船,其用材是经过认真选择的,在用材方面的安排也是很科学的,正所谓樟“高大,叶似楠而尖长,弥辛烈者佳,为大舟多用之”(〔宋〕梁克家:《三山志》卷四十二,土俗类四,物产,木)。
7.精巧的联接工艺
从泉州湾出土海船看,宋元刺桐海船的联接工艺也十分精巧。一是龙骨与艏柱的接连采用了直角榫合的工艺技术,具有美观坚固双重效果;二是船板上下左右之间都用榫接,并用铁钉加固,缝隙间都涂塞用麻丝、竹茹和桐油灰捣成的艌料,可使船体联结成坚固的整体,并有防渗漏功能;三是在木船的不同部位使用方、圆、扁不同形状的铁钉,采用“参”“吊”“锔”等适宜方法钉合,有效加强钉合部位乃至整个船体的强度;四是在钉合时还用钉送把铁钉送进木板深处,再用桐油灰将钉头密封,减少海水对铁钉的锈蚀,并提高船体的水密性。
使用铁钉加固以及桐油灰塞缝,是宋元福建特有的造船工艺技术,连邻近的广州民用海船也不具有。“深广沿海州军,难得铁钉、桐油,造船皆空板穿藤约束而成,于藤缝中以海上所生之茜草干而窒之,遇水则涨,舟为之不漏矣。”(〔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藤舟)伊本·白图泰对刺桐海船的铁钉加固技艺印象深刻:“先建造两堵木墙,两墙之间用极大木料衔接。木料用巨钉钉牢,钉长为三腕尺。”([摩洛哥]伊本·白图泰:《伊本·白图泰游记》,马金鹏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86页)使用铁钉工艺,需要较高的捻缝技术相配合,因此游历中国多年并熟知中西造船技术的马可·波罗十分推崇刺桐海船桐油灰塞缝工艺,“船用好铁钉结合……然用麻及树油(按,即桐油)掺合涂壁,使之绝不透水”(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三卷第一五七章)。
刺桐海船的木头榫联、铁钉加固以及桐油灰塞缝,是我国唐宋以来先进造船工艺的继承与发展,至今仍被普遍应用于木船的建造。与此形成对比,宋元时世界上许多航海国家的木船“惟联铁片”或“以铁镊露装”,尚未普遍使用铁钉加固。至于木头榫接和桐油灰塞缝这两种工艺,更是当时其他国家所未曾想到的,至多不过是“以椰子树皮制绳缝合船板,涂以橄榄糖泥的脂膏和他尔油”([日]桑原骘藏:《蒲寿庚考》,陈裕菁译,中华书局1954年,第95页)。或“取方相思合缝……惟以草塞罅漏而已”(〔明〕郑若曾:《筹海图编》卷八),以至于“不使钉、灰”的甘埋里(今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船“渗漏不胜,梢人日夜轮戽水不使竭”(〔元〕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甘埋里》)。上述船型、结构、属具和造船工艺等的分析表明,宋元刺桐海船具有的结构坚固、稳性好、抗沉能力强、航行设备完备等先进性能,为日后福船扬名海内外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宋元福建造船业的辉煌成就,与民间造船的兴盛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