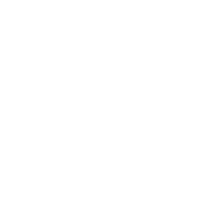万死一询众父老 岂为汉节始沾衣

清政府割让台湾以后,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大肆推行同化政策,其重点就是普及日语,逐步消灭汉浯,使台湾人民忘却祖国的传统文化,变成彻头彻尾的日本顺民。汉语在强大的同化压力下面临着灭亡的危险,而以汉语为表征的汉文化处于覆灭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台湾民众奋而捍卫汉文,为传统文化的保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
台湾第一任学务部长伊泽二在日军据台之初就确定了其殖民教育方针,“关于新领土之秩序的维持,……以威力征服其外形之同时,特别是非得征服其精神,去其旧国之梦,发挥新国民之精神,亦即非将其日本化不可,必要改造彼等之思想界,使之与日本人之思想同化,完全作为同一之国民。因而如此之精神亦即普遍教育之任务也。”在这个教育方针中,明确提出了同化台湾人民作为其最终的目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民族认同的标志之一,日本殖民者深知此道,因此对普及日语、排挤汉文非常重视,将其作为对台湾人民进行同化的重要一环。1896年,台湾人民武装抗日的硝烟还未散去,日本殖民当局便设置了一系列的“国语(日语,下同)传习所”,以“向土人传习现行国语,以为行政设施的准备,并为教育的基础。”国语传习所的第一条规则就是:“国语传习所所以教授台人国语,资其日常生活且养成日本的国民精神为本旨。”此后,这一措施不断强化。1898年,“国语传习所”改为公学校,专门收容台湾儿童。公学校设置的主要目的是向台湾儿童强行灌输日语,学生“从一年级开始起的大部分重点都放在熟练日语上”,而公学校的教师则严格要求使用日语。

同时,殖民当局不遗余力地打击汉文教育。一方面,尽力打击传统的汉文教育机构,如书房(私塾)、义塾等。另一方面,尽力淡化公学校的汉文教育。虽然公学校在1937年以前设有汉文科,但处于极不重要的地位。1898年《公学校规则》规定,汉文被置于读书、习字、作文中教授,教材增订有《三字经》、《孝经》、《四书》等。1903年修改《公学校规则》,汉文独立为一科,教学时数每周大约5个小时。1922年公布《新台湾教育令》,汉文被改为选修科,许多公学校趁机废除汉文。即使这样,汉文课程也不准自由教读,而必须用日本式的读法进行教学。皇民化运动开始以后,公学校的汉文科就被正式废除了。
日本殖民当局推行这种“日语中心主义”政策,为了不引起台湾人民过于激烈的反抗,开始时往往采取比较温和的手段。但当日语的推行遭到广大台湾民众抵制的时候,则依靠政治力量强力进行。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殖民当局开始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强行禁止汉语。台湾民众如果不讲日语就会被罚款,而在学校里学生如果不讲日语就会被长时间的罚站。汉文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在台湾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保卫汉文和传统文化的任务也更为严峻地摆在了台湾人民的面前。
二
日本据台以后,原来进行汉文教育的机构如府学、县学等均被废除,传统的书院也逐渐消亡,或是改变了生存方式。如上所述,书房也遭到了打压,然而因为其不属于官方机构,且数量庞大,一时难以全部废除,故而得以幸存,因此,书房也就成了日据前期台湾汉文保存的坚固堡垒。
书房的课程教育以传统的儒家经典为主体,如《三字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可以说是传统汉文最基础的教育机构。由于日本据台以后传统知识分子的仕途被堵塞,纷纷转向书房谋生,因而书房的数目一度膨胀。1903年以前在书房就学的学生均超过在日本所设的公学校就学的学生。书房对汉文化所起的承继和传递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著名史学家连横先生评价说:“沧桑后,汉文赖此以延生机。”台湾学者施懿林更是明白的说:“在早期,维系传统文化的重任,即由书房来负担,塾师们利用讲学授课之际,努力向学子灌输国家意识,民族情操,为的是保有我汉族的一股正气。”因此,书房成为台湾殖民当局民族同化政策的最大障碍,总督府处心积虑地打击书房,压制其发展。
1898年11月,总督府学务部颁布《关于书房义塾规程九条》,对旧有的书房进行整顿。规定书房虽然可以教授汉文,但应在教学内容和科目中逐渐加入日语及算术课程,必修的教科书必须由总督府指定。1921年颁布《书房义塾教科书管理法》,规定书房教科书的采用须经过各厅长批准。1922年颁布《新台湾教育令》,许多书房被取缔。通过这些措施,总督府一方面对现有书房进行改造,为其同化政策服务;另一方面则逐步减少书房的数量,直至最后取消书房,从根本上取消汉文教育。
尽管困难重重,书房的人还是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尽管总督府指定教材让书房使用,可是有的书房依然我行我素,不予理睬,依旧使用原来的教科书;或是表面应付,仅用日本人指定的教科书做一下表面文章;有的书房甚至暗地里使用当时祖国大陆编撰的教科书,令日本殖民当局大光其火。因此,尽管历经重重压制和打击,书房一直顽强地生存到了日据末期。虽然数量一再减少,但在汉文保存和传统文化的维护上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甚至在皇民化运动开始以后,书房虽已被全面禁止,仍有人在暗地里开设,直至1943年才被完全取缔,但这时距台湾光复已仅有一步之遥了。
三
台湾诗社起源于明郑时期,是当时文人之间保持联络、以文会友的一种民间组织。日本据台以后,为了笼络知识分子,对诗社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因此,随着书房的衰落,矢志于保存汉文的知识分子纷纷将目光转向了诗社。
许多加入诗社的知识分子表达了对诗社保存汉文和传统文化的期望。连横说:“盖以今日之台湾,汉学式微,群德沦落,文运之延赖此一线,自非纠集多士,互相勉励,不足以振弊起衰。”林献堂加入台北著名的诗社——栎社,就是出于利用汉诗来保存汉文的目的。
诗社经常举行诗会,众多诗人聚集在一起,共同切磋诗技,并有专门的刊物,如《诗报》、《藻香文艺》等,台湾的各大报纸也都为汉诗辟有专门的园地。同时,汉诗也进入寻常百姓家,平时百姓的婚、丧、喜、庆均有征诗纪念的情形。一时间台湾社会形成人人赋诗的奇观,民间社会的文学化程度的提高,为汉文的保存和发展提供了一个空间。
尽管人们对日据时期台湾的诗社评价不一,但是汉诗的广泛流行客观上为这一时期汉文的保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最为积极的意义在于培养了庞大的汉文读者群,从而使得广大民众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来接触汉文。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诗的价值已经超出了这种文学形式本身而具有保存汉族传统文化的功能,进而对于台湾人民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的保持都具有莫大的作用。
同时,诗社与书房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有的诗社直接就是由书房转化而来,或是由原来的书房主人设立的。如台北的“剑楼吟社”,
就是由著名的“剑楼书房”主人赵一山创立的。同样,新竹的“读我诗社”创始人叶文枢原来就是“读我书房”的主人,其社名系取自陶渊明的诗句“时还读我书”,意在于日本人统治下日日不忘读我汉文诗书之意。这种精神和书房传习汉文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四
面对着汉文在日本强大的同化攻势下濒临灭绝的局面,台湾的知识分子保持着高度的清醒和警觉。他们为汉文的生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除书房、诗社外,他们还通过多种渠道鼓吹和传播汉文。
首先是对汉文书籍的引进。在这方面,黄茂盛和庄垂胜两人的影响较大,取得的成绩也较为突出。黄茂盛是嘉义罗山人,对汉文极具兴趣,也十分热心于汉文的推广。1924年,他创设了“汉籍流通会”,购置汉文书籍数千种,供会友轮流借阅。1926年,更设置图书贩卖部,即“兰记图书部”,购置善本发售。同时代办上海所出版各种汉文书籍,如经、史、子、集、善书、佛经等,这是日据时期台湾中部最重要的汉文图书流通中心。庄垂胜创办的中央书局将贩卖中文书籍作为主要的目的,和商务印书馆等几家大的出版社都有联系。此外,台湾民族运动的领导人蒋渭水开办的文化书局影响也比较大。
其次,开办各种汉文讲习所也是宣扬汉文的一种重要方式。台南儒教团体“台湾彰圣会”设置“汉文讲习会”,聘请赵云石等汉学名家授课,主要讲述古文及儒家经典。组织者原来计划招收120人入会,最后入会者几乎是原计划人数的两倍,可见当时台湾民众对汉文学习的热情。蒋渭水也举办过类似的汉文讲习会,请连横讲解以书疏、传记、史论、文法字义、韵学等为主要内容的汉文知识。
即使在汉文全部被禁绝的皇民化运动时期,仍有知识分子顶着白色恐怖向民众传授汉文。台北市的赵鸿蟠,在皇民化运动开始后独创“剑书楼”,私印为日本人所禁止的汉文古文书籍,暗中课徒,“俾灌输中国传统文化于后学,期能保留我国传统文化于不坠。”林献堂也于皇民化运动开始后在日本的压力下教青年学习汉诗。
新文化运动也为汉文的保存和发展提供了新契机。“五四”运动以后,受祖国大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台湾知识分子也发动了文学革新运动,提倡白话文,希望以此将汉文在台湾发扬光大。20世纪20年代初,黄朝琴和黄呈聪以《台湾》杂志为阵地,鼓吹文学革新,开启了文学革命的先声。随后,张我军、赖和、彭华英、王敏川、蔡培火等纷起响应,形成了较大的声势。虽然新文化人士和传统知识分子在关于文学的观点上多有分歧,但是在保卫汉文这个问题上,态度却是一致的。
受此影响,1923年《台湾民报》(该刊物系由《台湾》杂志发展而来)增刊为半月刊,即决定采用白话文,“以平易的汉文,或是通俗的白话,介绍世界的事情,批评时事,报道学界的动静,……启发台湾的文化。”随后,随着发行量的不断扩大,1925年《台湾民报》又增刊为周报,1928年改称《新民报》,增刊为日报,成为日据时期唯一的汉文日刊,为推广白话文,保存汉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五
由于台湾社会处理日常事务和商业活动均是使用汉语,所以汉文在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若不识汉文,是和哑盲一样的苦痛。”殖民当局消灭汉文、强行推广日语的做法给台湾人民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因此,许多台湾民众宁愿将子女送到书房去学习汉文,而不愿送到日本的公学校就学。后来随着公学校的不断扩张与稳固,许多台湾人子弟迫于压力不得不到公学校就学,导致汉文知识越来越薄弱,甚至连基本的应酬书信都无法书写,为了以后生存计,家长不顾殖民当局的压力,“让其子弟进入私塾或是夜校就读,以学会日后赖以谋生的汉文。”当然,台湾人民对于使用汉语,这里重要的还是民族感情的因素。
所以,尽管日本殖民当局的同化攻势异常强大,但是台湾民众依旧坚持使用汉文,学习日文的积极性并不高。汉文仍是台湾社会的主要语言。台湾唯一的汉文日刊《新民报》在1937年之前的销售量就突破5万份大关,远较主要的三家日系报纸(《日日新报》、《台南新报》、《台湾新闻》)为多。即使是皇民化运动时期,人们虽然在公开场合不得不讲日语,但是在家中仍是以汉语(主要是闽南话)交谈。日本殖民当局虽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究无法将汉文彻底封杀,其割断台湾人民对祖国大陆依恋的企图自然也不能得逞。不屈的台湾人民虽然面临重重困难,还是将汉文保存下来,也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保存下来,虽然经历了50年的风吹雨打,他们的民族记忆依旧清晰,民族意识依旧强烈。梁启超先生在世纪初访台时写下“万死一询众父老,岂为汉节始沾衣”的诗句,对台湾人民的斗争予以极高的评价。以至于连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归结起来,(台湾人的民族意识)不外缘于他们原是属于汉民族系统,还极深厚地保有他们原有的语言、思想、信仰、以至于风俗习惯。”行文至此,想起今日之“文化台独论”者,面对历史,面对如此铁骨铮铮之先辈,他们能不汗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