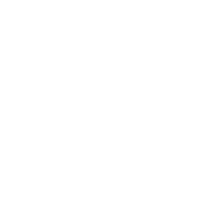孔子的“德治”与孟子的“仁政”

孔子画像
孔子没有说过仁政。起码,在《论语》中找不出这个词汇。从现存的儒家经典看,“仁政”这个概念,说得比较早、比较多,而且也比较系统的是孟子。
孔子之“仁”,既是道德观,也是政治观。孟子之“仁”,也具有此二重性。然而,孔子之“仁”与孟子之“仁”,又有明显的区别。孔子之“仁”,其涵盖面相当之泛,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人类美德。孟子之“仁”,却是有相当明确而清晰的边界的。《孟子·公孙丑上》云:“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的“四端”,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他所谓的“仁”,发端于人性之中的“恻隐之心”,即对于弱者的不忍之心。所以,孟子之“仁”与孔子之“仁”又有了其他几个方面的区别。一是要达到孔子之“仁”难度很大,所以,能被孔子称为“仁”的很不容易,即使在他的“高足”之中,还有不少是他“不知其仁”的,而孟子之“仁”,却是谁都可以做到的,因为这种“不忍之心”人皆有之。所以,孟子有“人皆可以为尧舜”之说,问题只在于你是否愿意去做。二是孔子之“仁”重在一个“礼”字,他相当强调上下尊卑等级观念。孟子之“仁”的指向,却在于一个“民”字。三是孔子之“仁”重在束“下”,而孟子之“仁”重在规“上”。
孟子所谓的“仁政”,就是从这种以“恻隐之心”为发端的“仁”字中引伸出来的。孟子劝齐宣王施行仁政。他对齐宣王说,听人讲过,大王您坐在殿堂上,有牵牛的人从堂下经过,您见了问道:“牛往哪儿牵啊?”那人答道:“要用它来祭钟。”大王您说:“放了它吧,我不忍心它战栗发抖,那是没有罪而被处死。”在齐宣王承认确有此事之后,孟子接着说,大王您有这种不忍之心,就足以实施仁政了。这道理很简单,对牲畜都有不忍之心,不愿无辜加害于它,难道对黎民百姓反而没有这种不忍之心吗?“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即“王之不王”,原因在哪里呢?孟子的结论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参见《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规劝君主们实施仁政,主要是规劝他们薄敛赋税、减省刑罚、慎用刀兵。他希望统治者能像对待自己的老人与幼儿一样地对待百姓,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他对他们提出的要求,都与一个“民”字密切相关。
一是与民同乐。齐宣王喜欢音乐,孟子对他说,问题的关键不是“好先王之乐”还是“好世俗之乐”,而在于“独乐乐”还是“与人乐乐”,是“与少乐乐”还是“与众乐乐”。他假设说,假如大王“鼓乐于此”,百姓闻乐而怨声载道,原因就在于不能“与民同乐”;假如大王“鼓乐于此”,百姓闻乐而脸有喜色,原因就在于“与民同乐”。(参见《孟子·梁惠王下》)
二是为民负责。按照孟子的观点,无论是君王(例如齐宣王)还是地方官(例如孔距心),都应当为自己所管辖的地方的百姓负责。倘若在你管辖的地方,年老体弱的奄奄一息,年轻力壮的四散逃难,那就是你的失职或渎职,即使是遇到灾荒,也难辞其咎。他打比方说:好比是领受了他人的牛羊而为其放牧,一定要为牛羊寻找牧场和草料,做不到这一点,就得把牛羊还给它们的主人,怎么能看着它们死去呢?(参见《孟子·公孙丑下》)
三是以民为本。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一条是最重要的,与民同乐,为民负责,便都由此派生。他认为,先有万民的拥戴,方有社稷方有君王。就是对于“齐人伐燕”之是非,也从“燕民”的意愿来考量,认为“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并将后者比之于文王事殷,将前者比之于武王伐纣。(参阅《孟子·梁惠王下》)

孔子主张在诚实守信的基础上,灵活通变,不拘泥教条。
孔子虽然没有说过“仁政”二字,但“仁政”却是孔子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说法有所不同。孔子称之为“德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论语·为政》);孟子称之为“仁政”——“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也”(《孟子·梁惠王下》)。此二者可谓一脉相承。孔子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论语·子路》)此中的王者,乃是实施德治之人;此处所说之“仁”,即为“仁政”。他说的是,王者实施仁政,大致也要有一个三十年的过程。
孔子的“仁政”(德治)与孟子的“仁政”,其内容并非完全一致。在孔子的为政之道中,“正名”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子张问政于孔子,孔子的回答是:“居之无倦,行之以忠。”也就是说,居于官位不懈怠,执行君令要忠实。这两章均在《论语·颜渊》之中。可见,孔子把君主看得很重,绝对说不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那种话来的。所以,武王伐纣,在孟子看来,并非“以臣弑君”,而是“诛一独夫”。孔子对此“以下伐上”之举却是有所保留。所以,他认为韶乐尽善尽美,而武乐尚有缺憾。
当然,孔子与孟子之间,也有诸多相通之处,
《论语·颜渊》中有一章说:“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期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可见在孔子看来,粮食、军备以及老百姓对于统治者的信任三者之中,信任是最重要的。如果失去了这种信任,那么,国家也就无法立足于世了。在《论语·颜渊》中,还有一章:“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有若是孔子的弟子,他奉劝鲁哀公用“什一”之税(即文中所谓之“彻”),不要再用“什二”之税,其实也是薄敛赋税,藏富于民的为政之道。虽是孔子弟子之所为,也可视同孔子的政治主张。

《礼记·礼运》中,开篇就是孔子与言偃(子游)说“礼”的一段文字,说的是夏商周之前的“大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由此可见,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仅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通,而且与“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暗合;而此处所说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也是孟子之“仁政”的理想境界。《礼记·檀弓下》中有“苛政猛于虎”一文,说的是孔子及其弟子在泰山之下之所见,形象地表达了儒家的政治主张。
客观地说,孔子所说的“使民以时”,虽不同于“爱”,却也是对于“民”的一种恻隐之心。这种恻隐之心,在其他方面也有所体现。例如:马棚失火烧了,孔子退朝回来,关心的是“伤人乎”,而不是马。((论语·乡党〉)又如,“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也就是说,不能让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普通百姓上战场去白白送死。孟子所说的“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孟子·告子下》),则直接脱胎于孔子此言。所有这些,对于后世之清官循吏的人本主义和悯农情结,都有深远的影响。
所以,尽管孔夫子没有说过“仁政”二字,后人说到“仁政”二字之时,却更乐于说是儒家的“仁政”,孔子的“仁政”,倒是很少说是孟子的“仁政”。在这种“仁政”之中,自有统治者的长治久安的愿望与老百姓的安居乐业的期盼之契合点。虽然很少能真正实行——在历史上,往往出现于改朝换代之际,体现于极少数具有民本思想的清官循吏的言行中——却也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
鲁迅的杂文中,对于孔子之“仁”,也是有所肯定的。1933年1月21日,周木斋先生在《涛声》发表《骂人与自骂》一文,说到北平的大学生“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应不逃难”。针对这一观点,鲁迅写了《论“赴难”和“逃难”》予以批驳。他说:“我是和周先生的主张正相反,以为‘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属于‘逃难党’的。”并且申述了自己的理由:
我们虽然也看见过许多慷慨激昂的诗,什么用死尸堵住敌人的炮口呀,用热血胶住倭奴的刀枪呀,但是,先生,这是“诗”呵!事实并不这样的,死得比蚂蚁还不如,炮口也堵不住,刀枪也胶不住。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我并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过觉得这话是对的,我也正是反对大学生“赴难”的一个。
从鲁迅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这样几点。其一,对于孔子此言,鲁迅可谓信手拈来,为我所用,相当熟稔。其二,鲁迅“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但也“不全”反对孔老夫子。对于孔老夫子,他是有所取而又有所弃的。其三,鲁迅觉得孔子“这句话是对的”,可以看作鲁迅衡量孔子学说的一个基准。对于不将民众生命视同于蝼蚁之命的其他体现人之恻隐之心的言论,也应在“对的”之列。所以,这也可以看作是鲁迅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孔子之“仁”或儒家“仁政”的认同。
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的仁政,都有其致命弱点。孟子游说君主实施仁政是为了他们称王天下,而这种仁政借以立足的基点,却仅是人的一种不忍(恻隐)之心。尽管这种不忍之心人皆有之,却并非可以强大到超越涵盖一切。因为人性之中,不仅有不忍之心,还有荀子所说的好利之心。《封神榜》里的西伯侯姬昌,忍痛吃了纣王送去的用他儿子伯邑考剁成的肉酱,造成纣王对他的错觉并放松对他的警惕,以保全自己的性命并成就自己称王天下的大业。这虽然只是小说家言,却也合乎情理。可见,这种不忍之心在利害得失的权衡之下的脆弱,而立足于这种不忍之心的“仁政”,又不免因为缺乏实力的支撑而显得空泛。你要贵为君主以至帝王的人,克制自己的各种欲望,去与民同乐、为民负责、以民为本,约束自己的荣华富贵去提倡并实施以“民为贵”而以“君为轻”的政治主张,岂非与虎谋皮?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句话符合历史的事实,却又是历史的一个误区。因为得人心可以让你得天下,得天下却往往使你不得人心。“得天下”者难免对天下的一切有一种强烈的支配欲和似乎是顺理成章的支配权,不仅是支配金银珠宝、绝色美女、万里江山,而且还要支配天下所有的人,包括他们的思想。稍有不从,便是忤逆。这便是得天下者失人心以至于最终成为众矢之的开端。